
诛心之论
杭州西湖旁有座岳王庙,是游人必到的地方。庙内有岳飞墓园。正对着岳飞墓的墙根下,有三尊赤裸上身、双手反缚、低头屈膝的铁像,那是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以及参与制造冤狱的万俟卨。过去游人到此,都要往铁像上吐唾沫,表示义愤。跪像始建于明武宗正德年间,距今已有四百多年了。秦桧等三人挨了四百多年的唾骂,倘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其实关于秦桧是有话可说的。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南宋立国之初,力量微弱,根本不足与金人为敌,他竭力促成和议,这想法本身并不是没有道理。把这一点抛开不论,单说岳飞的冤案,也不能把主要责任归在秦桧头上。按照宋朝的集权制度,大权都在皇帝手上,相权则很有限。如不是得到高宗的认可,或至少是揣摩并投合了高宗的意图,他岂敢以“莫须有”三字,杀害作为国家军事主帅的岳飞?不要说岳飞,就是杀一个县令,也未必如此容易。
但在岳飞死后几十年,孝宗为了推行北伐政策,为岳飞平反,将临安(即今之杭州)栖霞岭下的智果院改建为岳飞祠庙,宁宗时,又追封岳飞为鄂王(所以他的庙称为“岳王庙”),他渐渐从一个力主抗战的爱国将领被改造成忠孝节义的典范。不但他的死须得有人承担罪责,而且“忠”须得有“奸”作为反衬,这任务就不能不落在秦桧头上。又按照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凡败坏国家的事情,总有女人掺杂在内,所以又扯上秦桧的妻子。
自宋代建立岳坟和祠庙以来,诗人来到此地,多有题咏。这种诗在明代已经刻成了专门的集子。南宋叶绍翁的诗,主要是感慨岳飞的冤死和由此造成的北方的长期沦陷:
万古知心只在天,英雄堪恨复堪怜。如公少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
到了宋末元初的赵孟頫(子昂)的笔下,已经把岳飞的死同高宗君臣苟且偷安的态度联系起来。赵孟??是宋朝宗室,在他的想像中,如果岳飞不死,宋似乎就不会灭亡,所以情调尤其悲愤:
岳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但真正能够指出岳飞被陷害致死的实际原因,还是文征明的《满江红》词。当时有人从地下发掘出一块刻石,上刻宋高宗褒奖岳飞的手敕,文征明见了以后顿生感慨。词就从这里写起: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岂不念,封疆盛?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是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上片叹息岳飞的冤死。从石刻想到高宗起初对岳飞的倚重,再与岳飞后来的惨死相对照,由此显示高宗的刻薄寡恩。然后又从“功成身亡”这种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想到事已过去,后人发再多的议论,也毫无用处。这里作者的情绪似乎有些缓解,但缓解正是为了下一层高潮的涌起:尽管这是历史的旧案,与今人无涉,但想到风波亭(岳飞被害的地方)的冤狱,痛愤与悲哀之情,仍然无端地喷发出来。这一弛一张的笔法,令情绪更显强烈,也更显出害死岳飞之举的极端不合情理,使数百年以后的人,都无法忍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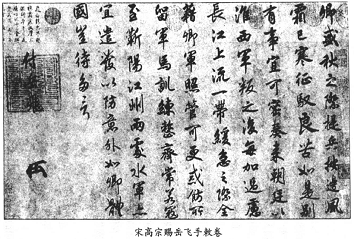 下片笔锋一转,追索高宗必欲置岳飞于死地而后快的原因:他身为皇帝,难道不想到小朝廷疆土迫促,正有赖于岳飞这样的良将恢复王朝的版图?他身为子弟,难道不想到父亲徽宗、兄长钦宗被金人俘虏囚禁的耻辱,正有赖于岳飞这样的义士为之洗雪?这些当然都想到了,但比起迎回徽、钦二宗而自己不得不让出皇位的结果,国家也好,父兄也好,都变得无足轻重。后人不要谈论当初高宗南渡是个失策,在他心里,却是害怕中原恢复!这里一句紧逼一句,揭出高宗的阴险心理。最后,又针对人们把罪责推给秦桧的说法,尖锐地指出:区区一个秦桧岂能害死岳飞?他不过是迎合高宗的欲望罢了!“逢其欲”三字,道出事情的关键所在,又置于篇末,短截有力,一字千钧。难怪清人毛庆臻在《一亭考古》中说:“此诛心之论。” 下片笔锋一转,追索高宗必欲置岳飞于死地而后快的原因:他身为皇帝,难道不想到小朝廷疆土迫促,正有赖于岳飞这样的良将恢复王朝的版图?他身为子弟,难道不想到父亲徽宗、兄长钦宗被金人俘虏囚禁的耻辱,正有赖于岳飞这样的义士为之洗雪?这些当然都想到了,但比起迎回徽、钦二宗而自己不得不让出皇位的结果,国家也好,父兄也好,都变得无足轻重。后人不要谈论当初高宗南渡是个失策,在他心里,却是害怕中原恢复!这里一句紧逼一句,揭出高宗的阴险心理。最后,又针对人们把罪责推给秦桧的说法,尖锐地指出:区区一个秦桧岂能害死岳飞?他不过是迎合高宗的欲望罢了!“逢其欲”三字,道出事情的关键所在,又置于篇末,短截有力,一字千钧。难怪清人毛庆臻在《一亭考古》中说:“此诛心之论。”
 文征明为人温雅,诗词也以委婉蕴藉见长,极少写得如此锋芒毕露,尖锐而激烈。不过,无须对此感到特别奇怪。《明史·文征明传》说他“和而介”,已经点出文征明外圆内方的性格特征。这首词,可说是“介”的集中表现。 文征明为人温雅,诗词也以委婉蕴藉见长,极少写得如此锋芒毕露,尖锐而激烈。不过,无须对此感到特别奇怪。《明史·文征明传》说他“和而介”,已经点出文征明外圆内方的性格特征。这首词,可说是“介”的集中表现。
还有,咏史诗词,大都不是单纯怀古或就史论史,而多少与作者的现实感受有关。明代自朱元璋立国始,就特别褒奖岳飞的忠君精神,作为强化君主绝对权威的一种道德手段。既讲忠君,就不能计较君主有无过失,于是把一切罪责,推给所谓“奸臣”。正德八年(1513,时文征明四十四岁),都指挥使李隆在杭州岳坟前始设秦桧等三人的跪像,就是这一意识的反映。文征明在词中指斥宋高宗才是真正的罪魁,恐怕是有意与社会舆论相对立,并且意识到那种社会舆论的真正用意。由此可以认识到,虽然文征明不像他的朋友祝允明那样经常显现出深刻的思考,但也绝不是一个毫无思想的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