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活割黄文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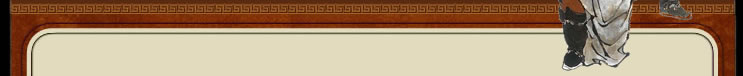 |
|
在《水浒》第七十三回中说到,李逵闹东京后,和燕青回返,途中歇宿到狄太公庄上。听说太公女儿房中闹鬼,李逵便冒充法师,骗了酒肉狂吃一顿,而后闯入闺房,一斧砍死了那个装神弄鬼的后生,又将太公女儿揪到床边,一斧砍下头来。接下来,只见:(李逵)把两个人头拴做一处,再提婆娘尸首和汉子尸首相并。李逵道:“吃得饱,正没消食处。”就解下上半截衣裳,拿起大斧,看着两个死尸,一上一下,恰似发擂的乱剁了一阵。李逵笑道:“眼见这两个不得活了。”
将人砍死后,还要剁着血淋淋的尸体来助消化,来娱乐,次日还强逼狄太公酒食相谢,这李逵可说毫无人性。李逵如此作为,和武松鸳鸯楼连杀十五人还不完全一样,后者起码在最初是被道德义愤驱上行动之路的,而李逵作践人尸体,却并不是出于对通奸二人的道德义愤,而是消遣娱乐,是赤裸裸的嗜血、野蛮、残暴。而故事的讲述人便如李逵的哥们儿一样,说起这事津津乐道,趣味盎然。
其实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已是不止一次讲述这类血腥行径了,如杨雄在翠屏山处置潘巧云,“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的”“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然后扬长而去。
此外,如武松的鸳鸯楼十五命,如清风山的燕顺等人挖人心做酸辣醒酒汤,如李逵的活割黄文炳,等等,都是。书中细述了李逵炮制黄文炳的过程,“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偌大的活人,绑在那里,如享用生鱼片般血淋淋边割边吃,在下不知若是列位看官身当其境会有何观感。
说到这,也许会有哪位朋友提出异议,说这黄文炳本就是个反动人物,阴险小人,本就该死,你替这厮叫甚么屈?
是吗?如果这样说,在下倒要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黄文炳是否真的该死?
黄文炳人品是极差,说他是阴险小人,也是事实,但问题是,他身为一个官府中人,发现有人公然在饮食营业场所题反诗,并且叫嚣要“血染浔阳江口”时,是否有义务向当地官府报告并穷究到底清除隐患?这个问题古人便有争议,多数是不认可黄的为人,但认可他的作法。那么今天这个问题该怎样看,在下不做答案,请列位看官、列位朋友自己思考;第二个问题是:就算黄文炳真是的该死,是否就该被如此残酷地活剐?
如果说“是”,那么在下就提第三个问题,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是否可以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而行使残忍的手段?
如果有哪位朋友还说“是”,那么在下便提第四个问题:请问,什么是高尚?是上天厘定的一个放之四海的先验的准则,还是是非由人自定?事实上,古往今来无数光天化日下的暴行有哪些不是在“高尚”的旗号下进行的?为了皇帝万岁,为了日尔曼民族的纯洁,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了革命,为了保卫伟大领袖,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只要目的是神圣的,手段的卑劣和残忍就都不成其为卑劣和残忍,就都是必要的,这样的逻辑,在人类的历史中带来的灾难难道不比单纯鼓吹暴力的强盗逻辑远为巨大和可怕?
而且,水浒世界里的很多血腥气冲鼻的行为,连追求正义的幌子都没有,完全是为蛮荒的嗜血心理所驱使,如本节开头提到的李逵的所为。
这样的情节,也不是《水浒》的专利,如唐传奇《虬髯客传》中的虬髯客豪气冲天地将仇人心肝切了以后生吃了下酒,如清代夏敬渠的《野叟曝言》中说到如何享用人脑:就是将早已打就的一支铜管伸入人脑,骨嘟嘟一吸,便如今日喝酸奶一般,将脑髓吸进肚里。
列位看官不要把这些都当作小说家言,实际上,中华民族确实有悠久的吃人历史以及虐杀传统。
首先,翻检史书,可以开出一长列吃人的名人清单:如春秋时雄才大略的齐桓公,吃了红案大厨易牙先生烹制的婴儿肉,对这位将自己儿子烧成大菜的厨子提出了表扬;如汉高祖刘邦,将开国功臣勇将彭越杀了后,把他剁成肉酱“分赐诸侯”;如后赵石邃发明了一道大菜,以美女肉与牛羊肉合而烹之;如隋炀帝在一次朝会上把一个不听呵(he)的大臣,烧成一道大菜,分给百官;如明代太监高寀为使阳道复生,吃小儿脑千余;……除了这些身居高位者的“精致”吃法,因战乱饥谨而导致的大规模的吃人更是史不绝书,正如鲁迅先生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
除了吃人,中国历史上更有种种名目繁多的虐杀,如车裂,如凌迟,如腰斩,如抽肠,如剥皮,如点天灯,如汉高祖的吕后将戚夫人弄成了人彘,如前秦时的苻洪剥了人面皮后仍让人歌舞,如明代朱棣攻陷南京后疯狗一般地用剥皮术、轮奸术残害建文帝旧臣及亲族,如张献忠大掠湖北、四川时剁下人手足堆积如山,等等,这些内容在下实在不便做稍细致一点的描述,如果这样做了,说不定就会有哪位朋友吃不下饭。
说到这里,想起了过去偶然读过的两本书。一本是作家梁晓声的自叙传《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书中说到文革时,一伙造反派将对方势力的一个成员扔进了滚热的沥青锅里,被害者的亲人子女在旁急得用手伸到锅里,一捧一捧地往外捞沥青;还有一本是美国亨利·莫尔上校的《越战纪实--女人·战争的受害者》,看这本书的时候,简直如在人间地狱,我并不是说书中描写得如人间地狱(当然事实也是如此),我是说我自己当时便如在地狱中,压抑得透不过气,放下书,如梦游般走到室外,好半天才恢复清醒。
前一本书说明虐杀的传统并没有随历史而远去,后一本书说明,人性中自有凶残与狞恶,非独中国为然。
所以问题不在于故事的叙述里有没有嗜血凶残的内容,这本就是人性的真实,而在于以何种立场来叙述,有没有反剩上面提到的两本书尤其后一本对此做了比较深刻的反剩中国古人也不是没有对此反省的,如司马迁的《史记·吕后本纪》写到: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帝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
正如夏志清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尽管司马迁对吕后残害行为的描写颇为客观,但当他写到吕后的儿子的强烈的反感时,已对吕后做了永久的判决。《史记》肯定文明事业;而《水浒》在对英雄们采取的野蛮报复行为大加赞赏时,却并不是肯定文明。”
不要怪夏志清先生喝多了洋墨水就回过头来挑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梁山好汉的理,实在是因为一部《水浒》中,值得我们今人深刻反省的内容是太多太多了。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