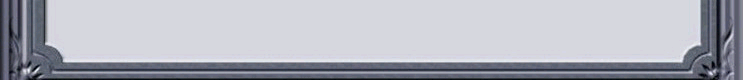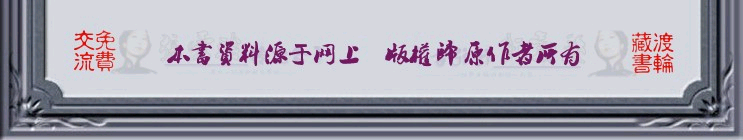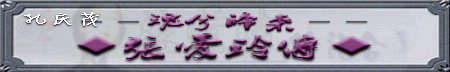
第十章 飘泊天涯
1.又见香港张爱玲
第二次又来到香港,但这一次和上次的心情却大不一样。
香港照例是陌生的,但她不怕,已习惯这陌生的世界,陌生中又有自由,“楼下公鸡啼,我便睡”,像《日出》中陈白露那样日晏高卧,更重要的是她可以卸掉一切的政治顾虑,尽情地写自己的东西,想怎样写就怎样写,即使她随心所欲地骂共产党的坏话,也没有别人来干涉她。她为自己获得的这种自由而庆幸,把在大陆上的见闻和牢骚不满通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
张爱玲到香港后,初期寄居于女青年会,设在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加锡知道张爱玲的文名,能写一手漂亮的中文,又具有英语功力,便邀请她为香港的美国新闻处翻译作品,稿酬很优厚。为了生计,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她也非常乐意干。美国新闻处请她把台湾作家陈纪滢的反共小说《获村传》译为英文。她还替美新处用中文译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玛乔丽。劳林斯的《小鹿》(后改名为《鹿苑长春》),根据马克。范。道伦编辑的《爱默森文集》编译的《爱默森文选》,华盛顿。欧文的《无头骑士》等。张爱玲对这些翻译的兴趣并不高,她说:“我逼着自己译爱默森,实在没办法。
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又说:”译华盛顿。欧文的小说,好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说话,无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只是迫于生计而已。但是她庆幸的是,在这里认识了一位也是做翻译工作的女同事——邝文美。邝文美是学者宋淇的夫人,宋淇(笔名林以亮)与夫人四十年代在上海时就是张爱玲的忠实读者,那时和上海的许多知识界人士一样,迷上了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等,很想见见张爱玲,但听说张爱玲脾气很怪,不喜欢与人往来,也就无缘相识。
他听夫人说现在张爱玲就与他的夫人在一个机构工作,志趣相投,关系还不错,大喜过望,便由夫人作介,认识了张爱玲。这样的萍水相逢,张爱玲与宋淇夫妇从此成为最好的朋友,终生的知音,这恐怕也是缘份。张爱玲所供职的美国新闻处是美国新闻署设在香港的窗口。五十年代初,由于美国出兵朝鲜,中国开始了抗美援朝的战争,中美两国在朝鲜问题上针锋相对,关系恶化。美国新闻舆论反华气势甚嚣尘上,张爱玲在这里工作,不可能不受这种政治舆论的影响。更何况她逃离大陆时本来就对共产党的统治心怀不满,她的思想与感情在她所写的作品流露出来,带上了一定的政治色彩。
张爱玲在翻译之外,开始了用英语写小说,她首次用英文写了长篇小说《秧歌》。
这部小说描写的是大陆土地改革之后的农村生活。土改之后,月香由在上海做帮佣而回乡生产、她本来是满怀着希望回去的。但是回家后发现,尽管分到了土地,她的丈夫金根还是村里的劳动模范,但家里却非常贫穷,全村都受穷受苦吃不饱。她在上海积攒的一点钱,亲戚邻舍还要来借。金根的妹妹金花出嫁了,丈夫家里更穷,他们兄妹两人从小是孤儿,相依为命,感情一直很好,金花来借钱,金根想借给妹妹点钱,但月香不肯,甚至也不给金花做一顿干饭。夫妻两人为此事生气。
但是他们的一点钱还是留不下来。快过年了,村里干部要求每家拿出四十斤年糕、半只猪去慰问军属,没养猪的要出钱。村干部王同志来做工作,说因为金根是劳模积极分子,动员他带头出钱,但金根说家里没有钱,两人吵闹起来,月香怕闹大了,赶忙拿出钱来,息事宁人。
然而金根还是很积极地做年糕交上去了。金根交去的年糕过秤时,王同志刁难他,说不够斤两,他与王同志又大闹一场。在旁边观看的人为交年糕的事不平,群情激愤,借机起哄,吵着要政府借钱过年。一群人拥到民兵镇守的仓库要抢粮,眼看乱得不可收拾,民兵们开枪威胁,向人群中扫射,枪声一响人群向四处奔散,在混乱中,金根受了重伤,女儿阿招被人群踏死。
当月香拉着丈夫到金花家去躲避时,金花对嫂嫂心怀不满,又怕连累到自己家,不肯收留他们,甚至不去看她哥哥。月香只好拉金根到别处藏身。
金根因为自己闯了大祸,难以逃脱,又怕连累了月香,就投水自杀了。月香万念俱灰,死去了女儿,又死了丈夫。她失去了理智,纵火烧了粮仓。大火被扑灭了,而月香本人已被烧死。
风波过后,新年到了,人们照样地扭着秧歌,抬着礼品挨家挨户去慰问军烈属了。
这篇小说是张爱玲以《人民文学》一篇文章梗概为轮廓,拼凑些道听途说的“根据”,或从报纸正面宣传中看出反面的材料,加上虚假的想象力而完成的,因此它违背时代的真实感。其实质是歪曲历史事实,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
张爱玲起初住在女年青会,独居一室闭门写作,她的名声渐渐大了起来,有人知道她就是四十年代上海文坛上大红大紫的才女张爱玲,便登门拜访。
张爱玲最怕打扰,托宋淇夫妇在他们家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换个别人不知的处所。这个斗室陈设异常简陋,屋里连书桌都没有,更没有书橱,也没有书。
张爱玲每晚坐在床上,就着床边的小台几写稿。她是一个来去无牵挂的人,“我故意不要家里太舒齐,否则可能:(一)立刻又得搬家。(二)就此永远住下去。两者皆非所愿。”这样没有负担,专心写作。那时她正在写另一部中文长篇《赤地之恋》。
《赤地之恋》完全是美新处授意她写的,由于美国的反华立场,想要她写这么一本反对共产党的作品。大纲已代她拟定好了,她没有自我发挥的余地,比起《秧歌》来,她更没有实际的生活经验和素材,写起来十分不顺手,尽管她很认真对待,但仍没有把握,她又为《赤地之恋》求得一签,占得的结果是:勋华之后项降为舆台安分守己仅能免灾这自然是不好的征兆,但她还是硬着头皮把书写了出来,先用中文出版,再翻译成英文。美国的出版商果然对此书没有兴趣,她在香港《今日世界》社分别出版了中文、英文本,中文本尚有销路,英文版则很少有人问津。
《赤地之恋》的历史背景跨越了土改、三反、抗美援朝等历史阶段,以刘荃与黄绢的恋爱为主线索。主人公刘荃在大学时代本是有政治理想与抱负的革命青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华北农村去搞土改,在这里,他看到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土改批斗地富,但村里地主富农不够数,为了完成上级的指标,把有些本不属于地富成份的中农也抓起来斗争,他的房东唐占魁是个中农,忠厚老实,政治上也是清白的,刘荃根据上边政策认为他不会有问题,但是唐占魁受到严刑逼供,最后被枪毙了。
刘荃觉得很负疚,但也无办法挽救,而且他还得随人一起参加对唐占魁的行刑。经过这一番打击后,他的理想破灭了,深感痛苦,与对现实同样不满的一位善良女子黄绢相爱,找到一点安慰。
土改之后,他又被调去从事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这里他更看透了现实的黑暗与丑恶,对一切都失去了希望。成为一个寻欢作乐的人,和穿着列宁装满口革命语录内心却情欲横流的女干部戈珊轧上了姘头。黄绢的到来使他又重新振作起来,就在这时,三反运动又开始了,刘荃无缘无故地被牵进了他的上司的案中,被抓起来关进狱中。戈珊想出一个“一石两鸟”的毒计,抖出张励为刘荃开脱罪责,又抛出毒饵让黄绢上钩。黄绢为了能救出刘荃的生命,迫不得已满足了一个权要人物的兽欲,以牺牲自己的肉体保住了刘荃的生命。
刘荃出狱知道后,痛苦万分,对共产党无比愤怒,他主动地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想在战争中忘掉这一切,战争中他被美军俘虏了。到了遣返战俘时,他本来可以选择到台湾定居,但却选择了回大陆这条路。“他并不指望再看见黄绢,但是他的生命是她的幸福换来的,他总觉得他应当对她负责,善用他的生命。他想不出更好的用途了。”他怎样“善用他的生命”,怎样才是“更好的用途”呢?
张爱玲在结尾写道:他要回大陆去,离开这里的战俘,回到另一个俘虏群里。只要有他这样一个人在他们之间,共产党就永远不能放心。
他知道反共战俘回去是要遇到残酷的报复的,但是他现在学乖了,他相信他能够胜利地通过这一切,回到群众中。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他不会永远是一个人。一万四千的战俘的坚决与勇敢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毫无疑问,这些近于煽动人们反共情绪的话一定是美国新闻处官员的“授意”所在。张爱玲这部小说最失败之处也就在于这里。
2.天涯路远
但无论如何,张爱玲《秧歌》、《赤地之恋》两部中英文长篇小说,在香港的小说界可以说影响不小。像她这样身居香港的一个中国人,能以英文小说打入美国并获得好评,实在不多见,在香港这块弹丸之地,真是凤毛麟角。张爱玲在香港再度走红。
她以前在大陆的《传奇》、《流言》以及其他作品纷纷被挖掘出来,在香港重新印行,不过大都是盗版,出版商看重她的名声,翻印她的作品可以牟取厚利,甚至有的人敢冒充她的名字写书。她很惊讶地发现有两部小说,一本《秋恋》,另一本《笑声泪痕》(又名《恋之悲歌》),书上署的名字都是“张爱玲”,而且书的名称也和她的书名相类似,写的内容也是男女情爱的一类,书里的主人公也是活动在沦陷前后的香港或上海的人,模仿得几乎可以乱真。但写的却很粗糙。从《笑声泪痕》书后一篇陈影写的跋文,可以知道《笑声泪痕》又名《恋之悲歌》,作者是个男士,但却冒了“张爱玲”
这样的女性名字。真的“张爱玲”非常诧异,赶紧把自己的短篇小说收集起来,定名《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在天风出版社出版,以防人家再盗印或假冒。但假“张爱玲”却借了她的光,那本《笑声泪痕》在龙门书局和文渊书店印行多次,赚了一大笔钱。
使张爱玲苦恼的还不仅是这些,她知道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并不是可以永久栖身的地方,繁华都市下的文化却是荒漠一片。香港本地的文化是寥落肤浅的,充斥这里文坛的大多是泊来大陆、台湾、东南亚以及海外华人的作品,各色各样的作品都可以在香港翻印出版,所以表面上香港的文坛是五花八门热闹纷呈的,但却掩盖不住内在的空虚。香港人的文化趣味与素养也不是太高,尤其是狭小的城市生活空间更不适宜文艺创作,张爱玲在此也根本本做落地生根的永久打算,在写《赤地之恋》时就打算移居美国了。就在这时,夏衍还命唐云旌写一封信托人给她,劝她不要去美国,能回上海最好,不能,留在香港也好,但她也更无心再回大陆了。
那时宋淇在香港电影界从事剧本审查工作。香港影艺界红得发紫的天王巨星李丽华和他认识颇久,李丽华知道张爱玲的电影剧本在上海上映很轰动,而且知道现居香港的张爱玲与宋淇关系极好,便再三恳请宋淇为她作介,见张爱玲一面。李丽华当年在上海演出成名之作《假凤虚凰》(黄佐临导演)
与张爱玲所编的电影剧本同是一家电影公司出品,是文华公司继《不了情》之后拍的第二部片子,可以说对张爱玲慕名已久,只恨无缘相识。此刻她刚刚组建了丽华影业公司,打算独资拍片,渴望能有张爱玲这佯一流的作家编写剧本。但她害怕张爱玲不肯见,便缠着宋淇想办法安排一见。李丽华在香港本是人人皆知的女明星,她一露面,记者、影迷就会蜂拥而上,围她个水泄不通,所以也不肯轻易见别人,但现在她竟然纡尊降贵求见张爱玲,宋淇也为难,怕张爱玲如果断然拒绝便不好办了。宋淇慢慢地给张爱玲做工作,终于获得她的首肯,约定了一个时间,在宋淇家中见面。
那天下午,李丽华特地从九龙过海来到宋淇家,为了赢得张爱玲的喜欢,在装饰打扮上颇下了一番功夫,装扮得比电影上更漂亮。她等了相当久,张爱玲才姗姗到来,李丽华一改平日快人快语坦率直爽的说话风格,说话特别斯文,小心地恭维着张爱玲,简直有“强盗扮书生”之感。张爱玲对她的印像也特别好,“越知道一个人的事,越对她有兴趣。现在李丽华渐渐变成立体了。好像一朵花,简直活色生香。以前只是图画中的美人儿,还没有这么有意思”。
但坐了一会儿,张爱玲就托辞有事先走了。她那时正在写《赤地之恋》,同时又申请移居美国,实在无暇顾及写剧本。她与李丽华仅止于惊鸿一瞥的缘份。
1955年秋,张爱玲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港赴美。到码头送行的只有宋淇与邝文美夫妇二人,要离开这一对知心朋友的时候,张爱玲才真正有点舍不得。依依惜别后,船上遇见了上海本地人,她没有一丝亲热感,还心心念念地想着这对朋友,一到日本,立即给宋淇夫妇寄了一封六页纸的长信,说:“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时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
3.三见胡适之
张爱玲到美国时,她的好朋友炎樱已经移居美国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了,张爱玲一到纽约就与炎樱在一起,仿佛当年同在上海似的。
炎樱认识的一个朋友在纽约职业女子宿舍住过,通过这个朋友的介绍,张爱玲就暂时住进了这所由纽约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救世军是基督教新教办的社会活动组织,常在下层群众中举办慈善事业。纽约的救世军是救济贫民出了名的,这里几乎成为贫民收容所。
这个职业女子宿舍临时收容了许多贫民、孤儿、酒鬼、无赖,又脏又乱,餐厅里管事的老姑娘都称作中尉、少校,代斟咖啡的是常醉倒在包艾里(The Bowory)的流浪汉,有个小老头子,蓝眼睛白蒙蒙地,有气无力地靠着咖啡炉站着。连住在这里的年轻女孩子们提起来也都讪讪嗤笑。张爱玲混迹于这些人中,真是不习惯,但新来乍到,也没有办法,好在常与炎樱在一起玩,多少减轻一些落魄之感。
到纽约后,张爱玲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去拜访她心仪已久几度通信的胡适之先生,去见见这位对自己奖掖有加的文学先辈。
还是在香港的时候,张爱玲的长篇小说《秧歌》刚刚出版,她想起她母亲、姑姑包括自己常常景仰的文学前辈胡适,就把这部。小说寄给了他,想请胡适对自己的作品提出批评意见。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他非常博学,对文、史、哲都有独到的见解,荣获过三十多个博士学位。他又是美国大哲学家杜威的入室弟子,杜威到中国讲学,他不离左右如影随形。在中国近现代文坛上可以说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胡适与张爱玲还是世交,他的父亲与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有过交谊。张爱玲的母亲与姑姑又很崇拜胡适,也与胡适有过一面之交,以前和胡适同桌打过牌。在张爱玲还未出生的时候,胡适已是中国文坛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了,她读书时,国文课本上就有胡适的文章。1946年9月,胡适辞去驻美大使之职在美国讲学三年回来时,姑姑在报纸上看到胡适从飞机上走下来的照片,笑道:“胡适之这样年轻。”但张爱玲始终没有机会拜见这位大学者。大陆解放前夕,胡适又乘船去了美国。张爱玲从朋友处得知胡适此时正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任馆长,便寄了一本《秧歌》给胡适。
此时的胡适,已是文化上的“挂冠部长”、“解甲将军”,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这个很不知名的图书馆任馆长。所谓的“馆长”,手下只领着一个助手,整日无事可干,正像夏志清所说的“游手好闲”。不久之后卸了“馆长”任,更闲着没事做,时常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翻阅各种大大小小中文报纸,甚至馆中赠阅的《侨报》,他也每天都看,每版必阅,连副刊的角角落落也不遗漏,偶尔还做点小笔记或评点。胡适在无聊之中,收到张爱玲从香港寄来的《秧歌》一书,十分高兴,他竟一连看了两遍,还在书上加了圈点与眉批,并给张爱玲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说:你的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作书名,写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功夫。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难得一般读者的赏识的。
《海上花》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好例子。你这本小说出版后,得到什么评论?我很想知道一二。
……我读了你十月的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像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读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是产生了你的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是十分满意了。
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时,我很想看看。……
胡适并在她《秧歌》一书的扉页上写了一段题词,把《秧歌》推为“近年我读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
这位连茅盾、巴金、老舍的长篇小说都不大看的文学大师,对她这个小辈如此誉扬,使得张爱玲受宠若惊。其实胡适推崇她的作品一半是因为她的小说的艺术造诣,令胡适惊喜,还有一点原因是小说对共产党的攻击。胡适因为在国民党撤退大陆之前曾以自己私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劝毛泽东不要把国民党逼上绝路,毛泽东不予理睬,挥师打过长江。他对共产党用武力赶走国民党很不满。因此,他对反共的作品是欢迎的。同时期台湾一个青年作家姜贵也把他的反共作品《今杌传》(后改名《旋风》),寄给胡适,尽管姜贵的作品艺术上相当粗糙,胡适也有兴趣地看了,还写长信对他表示“敬意和谢意”。但张爱玲是不大知道这些的,她只是感激胡适的知遇之恩。
到纽约不久,张爱玲便拉了炎樱一道去拜访胡适,因为她人很拘谨,有了炎樱这个比较活泼大方的人,感觉似乎好得多。
在纽约东城区八十一街上,一排水泥砌成的白色小洋楼像一个个方盒子,门洞里现出楼梯,完全是港式公寓的房子,在秋日午后的阳光里显得更洁白、更清静。她与炎樱感到有些恍惚,仿佛又回到了香港。上得楼来,忐忑不安地,她们不知道这个将要出来的著名人物该是什么模样。
胡适开门出来,热情地迎进她俩在客厅坐下。张爱玲看到这位六十又五的学者一点不显得老,身穿长袍子,戴着眼镜,神采熠熠,头发整整齐齐地朝后梳着,很有一种学者的风度。
胡适很爽朗笑谈着,张爱玲是见了生人就不大会讲话,显得很拘谨,人又高大,拘谨得手也不知怎么摆,脚也不知怎么放好。
胡适太太江冬秀为客人沏好了两杯浓郁的绿茶端进来,张爱玲看到这位当年由父母包办许配的胡太太,依然露着年轻时的端丽的丰韵。江冬秀很白,虽然年龄大了,但圆脸上的皱纹一丝一丝很细腻,头发向后梳着,没有一丝乱发,头发后边绾着光滑发亮的圆髻。江冬秀的话略带点安徽口音,张爱玲听着更为亲切些,看来胡适这个新式人物的旧式婚姻,仍是很美满的。她立刻又想起以前颇为流传的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佳话来。1917年,已做了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遵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回乡与这位旧式小姐结婚,一时众人议论纷纷。江冬秀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却很聪明美丽,人又大方,到现在依然风韵犹存,难怪胡适后来能与她恩恩爱爱白头偕老呢。
张爱玲看着眼前这对老人,看着他们室内的陈设,她想到了上海,想到自己的家。小时候她父亲的书桌上就摆有《胡适文存》,与较不像样的狎邪小说《歇浦潮》、《人心大变》以及《海外缤纷录》等摆在一起。这些乱七八糟的小说她是一本一本地拖出去看的,只有《胡适文存》是坐在父亲窗下的桌前看完的。眼前,过去,时空像一叠叠照片重叠在一起,她从记忆中搜出些话题与胡适交谈。
炎樱也用国语找出话来填补无活的空间。炎樱的几句中国话本来就是半通不通的,又离开上海许多年,更不大会说了,但她那副活泼自如的神气很招人喜爱,胡适与太太很喜欢她,慢慢地用国语同她俩交谈。
张爱玲又想起她姑姑以前跟父亲借书看,后来兄妹闹翻不来往了,父亲有一次忸怩地笑着咕噜了一声:“你姑姑有两本书还没还我。”姑姑有一次也不好意思他说:“这本《胡适文存》还是他的。”还有一本萧伯纳的《圣女贞德》,德国出版的,她姑姑很喜欢那米色的袖珍本,说“这套书倒是好”。
张爱玲忽然想起旧事,壮着胆子,幽幽地问:“您还记得我母亲和姑姑么?
她们以前还跟先生同桌打过牌呢。“
胡适很惊讶:“有这等巧事?”他很注意地看看张爱玲,仔细地回想,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因为他的太太是个牌迷,没有事情时,常常打麻将消遣,胡适的朋友太多了,各界都有,凑到一起没事干,也爱打着玩。
胡适由张爱玲《秧歌》和去年的信谈到英译小说,对张爱玲准备翻译《海上花》与《醒世姻缘》很有兴趣。对她说:“张小姐想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这个志愿很好呀。以你的文学功底,我相信你能做到。
不过,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要准备吃点辛苦喔!“
“我会用心努力去做的。”胡适的谈话增强了她的自信心。
“你怎么会对这两部作品感兴趣呢?”胡适笑着问她。
她说:“反正从小就喜欢。《海上花》似乎是父亲看了您的序文后买来的亚东版。《醒世姻缘》是后来我读了您的《考证》后破例向父亲要了四块钱买的。”
胡适很惊讶地笑道:“你记得这么清楚?”
张爱玲不禁也笑了,说:“我还记得买回来后,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先给他一两本,我从第三本看起,因为读了你的考证,大致已经有点知道了。前几年我去香港读书,正遇着港战,当了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了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就埋着头看起来,一连看了几天抬不起头来。那时图书馆房顶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的目标,炸弹一颗颗轰然地落下来,越落越近,我还在想,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胡适听了张爱玲的这两句话,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番谈话后,张爱玲觉得胡适真是和蔼可亲的老人,像一个年长的慈父一般,对后辈这么关怀。她也感觉到晚年在美国作寓公的胡适似乎很落寞。
后来,她又一次去看望胡适。她参观了胡适的书房,这位大学者的书房里沿墙一排顶天立地的书橱,全是一叠叠夹着许多零乱纸片的文件夹,显然都是胡适做的札记,她觉得他的书房有一种铺天盖地的压力,看着就觉得心悸。
胡适仍是非常和蔼热情。在他面前,张爱玲觉得自己太渺小了,也许是从小就崇拜这位学者的缘故吧,跟胡适谈话,觉得如对神明,话也不敢多说,口将言而嗫嚅,她感到更拘谨。
胡适和她随意地漫谈,不知怎么说起大陆来,胡适说:“纯粹是军事征服。”张爱玲深有同感,她自从三十年代起看书对左派就有本能的反感,开始写东西时,她就一直站在政治潮流的外面。她的《秧歌》、《赤地之恋》所表达的内容与胡适的思想可以说不谋而合。她顿了一顿,想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处说起,接不上话茬。胡适脸一沉换了个话题。
胡适告诉她:“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里书很多。”张爱玲笑了笑,虽然她也到过市立图书馆,但又不好意思地想自己从来没进过大图书馆,没有到大图书馆看书的习惯。这话自己都不好意思开口。
“说起来,我与你两家还算是世交呢!”胡适接着说:“我的父亲与你祖父认识,你祖父还帮过我父亲一个忙呢!”又说:“前几天还在书摊上看到你祖父的全集,只是没有买。”张爱玲很惭愧,虽然知道自己的祖父是张佩纶,但也只是知道祖父与李鸿章的小姐之间的婚事而已。适之先生的父亲是谁,她祖父帮过他父亲什么忙,家里的人从不跟她提祖父的事,她也一概不知。她翻过祖父的《涧于集》,但满纸的典故、人名、家常书信,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胀,也没有看出什么幕后的事情。她只好点点头:“嗯,是么?”实在只有听说话的资格。
胡适谈起他正在为美国《外交》杂志写一篇文章,张爱玲觉得可以找几句恭维的话了。但胡适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们这里都要改的”。
张爱玲听罢有点难过,像胡适之先生的文章谁有资格改呢?她感觉到这位长者内心的一份失落。但她又能说什么呢?炎樱见过胡适后,四处打听,问人知不知道中国胡适这个人,回来对张爱玲说:“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这样一个中国新文化的奠基人在西方竟不被人所知,还不如林语堂,张爱玲的悲哀袭上心头。
这一年11月,最后的一个星期四,照例是美国的盛大节日感恩节。张爱玲与炎樱一起,到一个美国朋友家去吃饭,非常热闹,像中国的过年似的暖融融的,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谈,一顿烤鸭吃到天黑。从好客的主人家出来,两人在整洁而又冷清的街道上踱着,好像在当年上海的灰色街道上散步一样,一边走着,四顾街上的霓虹灯,各种明亮好看的橱窗,一边说着笑着。
张爱玲想起了上海的日子,但手挽着炎樱,她感觉很踏实,有这么知心的朋友,也就不大想故乡了。她们就这样在外面疯逛了一回,才回家去。
回到宿舍,张爱玲便伤风感冒,呕吐不止。恰在此时,胡适来了电话,原来是怕她一人节日里寂寞,邀她去吃中国馆子。她很感动,抱歉地告诉说她病了,胡适约好隔天来看她。
胡适果然如约而至,到这个杂乱无章的职业女子宿舍来看她了。人在他乡,有这么一个长辈关心她,她心里歉然而又温暖,感动得说不出什么话。
两人坐在偌大的公用客厅中,找着话题来说,一递一句地聊着。虽然感激,但她总像是有话说不出来,便一阵沉默,沉默也是一种交谈,无言的交谈与默契。
胡适要告辞了,她送他到门口,两人站在台阶上再说一阵子话,好像话还没说完,但开口谈几句,又是沉默,她送适之先生,最后再看看那个慈父般长者的背影: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地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臂,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张爱玲把这一刹那的感情写得如此动人。她感到了晚年胡适之的落寞的心境,她自己内心涌出从未有过的悲凉,人生苦短,客中送客,这种漂泊的人生更何以堪。
然而,她没有料到,这竟是她见胡适的最后一面。
次年2月,张爱玲离开了纽约,搬到美国最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去,便无法与胡适来往联系了。两年后,她申请到南加州亨亭屯。哈特福基金会一个半年期的名额。该基金会是A&P超级市场后裔办的艺文作场,专门接待文艺家。地点在一个风景秀丽的海边山谷里。按规定入基金会须有人作保而且至少需要七个人,张爱玲便写信给胡适。
胡适很爽快地答应了。也就在这时,台湾来函邀请胡适到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知道见到张爱玲的机会不多了,还是慷慨地为她担了保,并且把张爱玲送给他的《秧歌》寄还一本给她。扉页上,有胡适的题辞,里面有他对本书的圈点,行间页眉的空白处用细密的蝇头小楷批注,他把书给张爱玲,作为两人真挚友谊的留念。
捧着这本书,看着这密密的圈点批注,张爱玲感觉得很重,重得她负荷不起。她回信表示感谢,可是这满腔的感动感激之情简直无法表达,她这时才第一次感到自己以前那么绚丽的彩笔现在又是何等的生涩,写出来是干巴巴的语言,一点也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无奈还是把这干巴巴的信寄了去。
1958年4月,胡适离开美国,回台湾去了。张爱玲时时刻刻地挂念着这位长辈,从报纸上寻找胡适之先生的消息。
1962年2月报纸上传来噩耗:胡适之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酒会上心脏病猝发逝世”。张爱玲悲痛难忍,几年后把她的感情寄托在一篇深沉悲凉的散文《忆胡适之》里,向他致以最心痛的祭奠。
她没有忘记自己对胡适说过的志愿,也没有忘记胡适对自己的希望与勉励,因此像还债一样,把《海上花》这一部吴语方言小说译成英语和国语,每提起笔来,就会想到胡适先生不在了,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因为那种怆惶与恐怖太大了,想都不敢朝上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