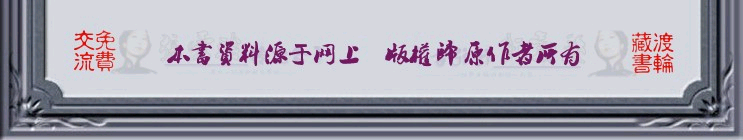第二章
一篇写了二十多年的小说——《色·戒》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一日,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在《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发表了,后来张爱玲在一九八八年皇冠出版的《续集》的《自序》中说,《色·戒》是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构思的。而在一九八三年皇冠出版社结集张爱玲的《色·戒》《浮花浪蕊》《相见欢》《多少恨》《殷宝滟送花楼会》《五四遗事》和电影剧本《情场如战场》合为《惘然记》一书出版,张爱玲在序中谈到《色·戒》《相见欢》和《浮花浪蕊》时,说:“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因此结集时题名《惘然记》。”因此我们得知《色·戒》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构思(当时张爱玲从上海来到香港),到一九七八年发表(当时张爱玲人在美国),其间历经二十五个寒暑。
《色·戒》发表后的将近半年,也就是一九七八年十月一日,张系国以“域外人”的笔名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一文,其中最后一段,张系国这么说:“我同意不用世俗道德的标准来批判文学作品。作家可以采取非道德超然态度写作,但分析到最后,作家还是会有各自的道德立场。不是所有不道德的题材都值得写,作家在取舍之间仍应有其原则。西方文学批评有一桩影响是不太好的。文学批评家(尤其今日欧美的文学批评家)常特别重视还没有被人写过的题材,认为写人所不敢写的题材就是‘突破’。但不是所有的不道德的题材都可以写或应该写。作家如果故意标新立异,特意发掘不道德的题材,也许反而会毁了自己。至少我认为,歌颂汉奸的文学——即使是非常暧昧的歌颂——是绝对不值得写的。因为过去的生活背景,张爱玲女士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尤其应该特别小心谨慎,勿引人误会,以免成为盛名之瑕。”张系国在文中虽然没有明指张爱玲为汉奸同路人,但他认为这种歌颂汉奸的文学是不值得写的。
说“汉奸”太沉重,于是从来不喜打笔仗的张爱玲,面对如此严厉的指控时,在一个多月后的十一月二十七日同样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一文,予以强烈反驳。张爱玲对自己的作品作出辩护的,除了一九四四年五月迅雨(傅雷)在《万象》杂志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五月一日出刊),而引来张爱玲立即在《新东方》杂志同年五月号(案:五月十五日出刊)中写《自己的文章》作出响应外,这是第二次。张系国的文章,就“政治立场”而言,显得深文周纳,有上纲上线之嫌,因此逼得张爱玲再也忍不住跳出作响应,因为“汉奸”之说,是她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我们知道张爱玲虽然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两年内,红极一时,在抗战胜利后,虽然没有被南京政府正式定为“文化汉奸”的罪名,但社会舆论却欲置她于死地而后快,她的文学活动甚至于私生活,都成为公众谩骂的焦点。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曾说:“抗战胜利后的一年间,我姐姐在上海文坛可说销声匿迹。以前常常向她约稿的刊物,有的关了门,有的怕沾惹文化汉奸的罪名,也不敢再向她约稿。她本来就不多话,关在家里自我沉潜,于她而言并非难以忍受。不过与胡兰成婚姻的不确定,可能是她那段时期最深沉的煎熬。”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胡、张两人初相见,而后很快就成为恋人。半年后,也就是一九四四年七八月间,胡兰成向第三任妻子英娣提出离婚,随后与张爱玲私下成婚。由于胡、张的婚姻关系,导致后来人们把胡兰成的汉奸身份,也加之于张爱玲的身上。
(2)
学者陈子善在《一九四五至四九年间的张爱玲——文坛盛名招致“女汉奸”恶名》一文中,就指出:“……可以想见,给张爱玲安上‘女汉奸’的罪名,泰半是因了胡兰成的缘故。《女汉奸丑史》和《女汉奸脸谱》中关于张爱玲的章节,连标题都如出一辙,前者为《无耻之尤张爱玲愿为汉奸妾》,后者为《“传奇”人物张爱玲愿为“胡逆”第三妾》。两文均言词尖刻轻佻,属于人身攻击,无稽谩骂。”(陈子善《1945至49年间的张爱玲——文坛盛名招致“女汉奸”恶名》,香港《明报月刊》,2006年12月)
除了这种未署名的小册子的恶意攻讦外,那时上海的大刊小报,类似的“揭发批判”更是不少。陈子善先生在同文又指出,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上海《海派》周刊就发表一篇署名“爱读”的《张爱玲做吉普女郎》的耸动报道:“……前些时日,有人看见张爱玲浓妆艳抹,坐在吉普车上。也有人看见她挽住一个美国军官,在大光明看电影。不知真相的人,一定以为她也做吉普女郎了。其实,像她那么英文流利的人有一二个美国军官做朋友有什么稀奇呢?”
另外还有一本署名“司马文侦”的《文化汉奸罪恶史》,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的。在作者的《几句闲话》后,先有《三年来上海文化界怪现状》《“和平文化”的“大本营”》、《沐猴而冠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等综述,接着就是对于“文化汉奸们”的“个别的叙述”,张爱玲在书中被两次“点名”,一是在揭发《伪政论家胡兰成》时被提到,另一次则是被单列一章——《“红帮裁缝”张爱玲:“贵族血液”也加检验》。司马文侦在书中指责“文化界的汉奸,正是文坛妖怪,这些妖怪把文坛闹得乌烟瘴气,有着三头六臂的魔王,有着打扮妖艳的女鬼”。他主张对这些所谓“文奸”(包括张爱玲在内)采取“有所处置”的行动。
对于将张爱玲与胡兰成绑在一起的做法,晚近的学者张泉在《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析》一文中,就指出:“胡兰成是胡兰成,张爱玲是张爱玲,不能因两人曾有感情纠葛而在政治身份的界定上实行封建制的株连原则。”
《文化汉奸罪恶史》将张爱玲和张资平、关露、潘予且、苏青、谭正璧等另外十六个作家列为“文化汉奸”,书中列数张爱玲的“卖国行为”、“罪恶事例”,指责她在《杂志》《天地》《古今》等“汉奸”刊物上发表文章,还参加一些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像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由《新中国报》主办的“纳凉会”等等。
我们知道张爱玲在走红的两年间,作品主要发表于《新中国报》系统的《杂志》月刊、《新中国报》副刊“学艺”,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月刊、周黎庵主编的《古今》半月刊、周班公主编的《小天地》月刊和由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创刊,后来编辑部移到上海的《新东方》月刊及由胡兰成创办的《苦竹》月刊等九大刊物中。其中除了《紫罗兰》及《万象》外,几乎都是与日伪有染的文学期刊,其中《新东方》是由曾任汪伪政治局局长的苏成德负责的,张爱玲投稿该刊可说是胡兰成牵的线,而《苦竹》更是由胡兰成所创办的。因此若从这点指责她投稿于汉奸主办的刊物上,显然是成立的。
(3)
当时曾经提拔过张爱玲,而刊登她的作品《心经》《琉璃瓦》《连环套》的作家柯灵在《遥寄张爱玲》文中,就说过:“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于文学而在于为自己撑场面。”而张爱玲的另一友人龚之方更说:“张爱玲非但是写小说的好手,而且是一名快手,作品连续诞生,刊登在各种报刊上,其时上海报刊的背景十分复杂,有的是接受国民党什么派的津贴办的,甚至有的与汪伪有干系的,张爱玲没有政治头脑,因此对发表园地也不去考虑是否合适。”柯灵又说:“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之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
我们知道当时的张爱玲正是创作勃发的时候,她又主张“出名要早”,于是有“趁热打铁”之说。而当时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些刊物外,已别无发表园地了。她要使自己的作品在短时间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就不得不有所依附,因此她对于这些指责,并没有任何的反驳。虽是投稿于所谓汉奸主办的刊物上,但她的笔端却没有写过半点歌功颂德的文字,这是不争的事实。当时张爱玲的心态,或许从她的好友苏青可得知一二,苏青对这些指责,有她的辩驳,她说:“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恰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无愧怍。”后来苏青更在长篇小说《续结婚十年》的扉页题词上写着:“衣沾何足惜,但使愿无违。”更有强力辩解的意味。
面对此问题,晚近的新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的看法,无疑是较中肯的,他说:“当然我们倾心赞赏大义凛然、抗战不屈的那些作家如李健吾、夏丏尊等,但是对于那些缺乏反抗勇气的人,笔者不忍概以汉奸指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毕竟是少数仁人豪杰的事情,不能用来衡量普通人。”(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75年)
《文化汉奸罪恶史》除了上述的指责外,更严重的是指责张爱玲出席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举行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如果说某些风言风语张爱玲还能保持沉默的话,对于指责她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借以证实她的“文化汉奸”的身份时,她就不得不开口,加以辩驳了。一九四六年底她借《传奇增订本》的发行,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为自己作了辩白,她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刊登的名单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
(4)
我们知道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间,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策划召开了三次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其用意是想对中国沦陷区文学实施干预和渗透,企图将中国文学拖入“大东亚战争”里。其中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于南京召开。据学者王向远的资料( 王向远《“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日本对中国沦陷区文坛的干预渗透》,《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3期),日本派出的代表有:长与善郎、土屋久泰、高田真治、丰岛与志雄、北条秀司、火野苇平、芳贺檀、户川贞雄、阿部知二、高见顺、奥野信太郎、百田宗治、土屋文明等十四名。中方参加人数则高达四十六名,其中“满洲国”代表有古丁、爵青、田鲁、疑迟、石军、小松,还有加入了“满洲国”的日本人山田清三郎、竹内政一,共八名;华北代表有钱稻孙、柳龙光、赵荫棠、杨丙辰、山丁、王介人、辛嘉、梅娘、雷妍、萧艾、林榕、侯少君等,共二十一名,周作人因高血压而不能出席。华中代表有陶晶孙、柳雨生、张若谷等二十五名,其中有不少并非“文学者”,而是汪伪政权中的官僚政客。列席会议的还有当时在南京的日本美术史家土方定一、诗人池田克己、作家武田泰纯和佐藤俊子,以及在中国开设书店的内山完造等人。张爱玲实未参加,因此她不甘心被抹黑,特发表此声明,为自己辩护。其实在当时许多日伪的高官如宇垣一成大将及汪伪的熊剑东,都想借胡兰成的引荐而得识名噪一时的张爱玲,但都被她一一拒绝了。因此张爱玲无心和汉奸周旋,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有这些惨痛的教训,张爱玲对于“汉奸”的指责是极为敏感的。她实在不愿再重蹈覆辙,因为她的文章而连带有人对她的人身的指控,或许这也是她这篇《色·戒》写了二十多年的原因,她或许不愿她的敏感题材在敏感时刻再成为敏感的话题,于是她一改再改,一拖再拖,让时间冲淡敏感的氛围,终于在二十多年后才发表。但没想到还是引来了话题,于是她为文加以辩白,文章的开头,她说:“这故事的来历说来话长,有些材料不在手边,以后再谈。”似乎刻意避开故事来源的问题。而到了一九八八年她在《续集》的《自序》里,她对于当年与张系国的论战,更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被逼写出来的。不少读者硬是分不清作者和他作品人物的关系,往往混为一谈。曹雪芹的《红楼梦》如果不是自传,就是他传,或是合传,偏偏没有人拿它当小说读。最近又有人说,《色·戒》的女主角确有其人,证明我必有所据,而他说的这篇报道是近年才以回忆录形式出现的。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哪里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常百姓知道底细?记得王尔德说过,‘艺术并不模仿人生,只有人生模仿艺术。’我很高兴我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构思的短篇小说终于在人生上有了着落。”
在后来张爱玲这段文字里,她一直要避开《色·戒》故事情节是否“有本”的问题,她甚至以《红楼梦》为例,要人们将它当小说读。更以“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哪里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常百姓知道底细?”来辩驳,并说她这小说是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构思的,而当年的事件报道近年才以回忆录形式出现。这“以回忆录形式出现”的报道,当指金雄白(朱子家)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金雄白,字烯民,江苏青浦(今上海)人,一八九四年生。他原是跑政治新闻的名记者,早在一九二九年就是《京报》的采访主任。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他留在孤岛租界执律师业。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周佛海劝说下加入汪伪政权,一九四○年因帮周佛海办《平报》而成上海沦陷区炙手可热,显赫一时的媒体巨头。历任南京政府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中报》社副社长,南京兴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司法当局以汉奸罪名起诉,判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一九五○年移居香港,穷困潦倒,以卖文为生。一九五七年以朱子家笔名,为香港《春秋》杂志撰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以连载方式刊出,一九五九年结集出书( 罗久蓉《历史叙事与文学再现:从一个女间谍之死看近代中国的性别与国族论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1期,2003年12月)。张爱玲在此强调她是在一九五三年构思此小说的,在时间点远在金雄白撰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之前,因此金书非其所本。但在张爱玲改写的二十多年间,是否看过该书,我们不得而知,尤其是在六十年代张爱玲曾一度到香港写电影剧本。
(5)
说到金雄白倒有一事,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新中国报社”曾在上海咸阳路二号开了“纳凉会”的座谈会。当时参加者除了李香兰、张爱玲之外,还有日人松元大尉、中华电影副社长川喜多长政和炎樱、金雄白、陈彬龢等人。金雄白在会中曾问了张爱玲对小报的意见,张爱玲说她从小就是小报的读者,也在小报上写过文章,但不知为什么登了出来看看很不顺眼,所以还是想保持忠实读者就好。可见,金、张两人当年虽有交往,但并不投机。后来张爱玲对金雄白选择遗忘,而金雄白对张爱玲也语多讥讽。
但张爱玲这故事到底有没有“所本”呢?张爱玲一来说是“这故事的来历说来话长,有些材料不在手边,以后再谈”。这岂不是说此故事有出处吗?后来又说包括《色·戒》在内的三篇小说的素材,“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多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这不更证明《色·戒》等是有“所本”的吗?
加之张爱玲在一九七一年接受水晶先生的访问时,曾称“《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所本’的”,而张子静在张爱玲去世后所写的《我的姊姊张爱玲》书中,更明确地指出,《金锁记》的故事、人物脱胎于太外祖父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而《花凋》则是写张爱玲舅舅黄定柱的三女儿,也就是她三表姊黄家漪的故事。学者冯祖贻则指出,《创世纪》是以张爱玲的六姑奶奶,也就是祖母李菊耦的妹妹(任家)的故事为底本的,另外《茉莉香片》则活脱脱是上海张爱玲的家,主人公聂传庆就是张子静(当然也有张爱玲的投影)。张爱玲似乎并不忌讳道出小说的来历。
学者余斌认为:“张爱玲不是天马行空型的作家,其写作常需有所依凭,她的个人经验其实很有限,唯如此,她总是最大限度地充分加以利用,这里的经验有些是亲历,有些得自亲朋,有些得自书面材料,要在具有某种直接性,与己可产生某种关联……《色·戒》故事与她的关系看似远得多,但故事发生于她最活跃的那一时空,背景、气氛她自能有一种奇异的感知,间接里也就存着某种直接。对她这种孜孜于传达‘事实的金石声’的作家,这样的故事如没有原型,才是怪事。在此原型之重要,在于她可借此生动地延伸想象,曲尽其妙地达到生活的逼真性。”( 余斌《〈色·戒〉考》,《万象》杂志,2005年9月)
《色·戒》的“本事”,被指向一九三九年底郑苹如刺杀丁默村事件,当年在上海沦陷区是“遐迩喧腾”的大事,但那时张爱玲正在香港大学念书,有可能根本未曾听闻。那她的材料,得之何处呢?香港学者兼影评家陈辉扬在其《梦影录》一书中,就提出:“我一直认为《色·戒》的材料来自胡兰成,因为易先生和王佳芝的故事,是根据郑苹如谋刺丁默村一案而写成的。其中种种细节,只有深知汪精卫政府内情的人才能为张爱玲细说始末。”正如张爱玲所说的“平常百姓”是无法得知“敌伪特务斗争内幕”的,但因后来她与胡兰成的关系不是夫妻而胜似夫妻,两人相处的日子里,以胡兰成的话说常是“连朝语不息”,当然这其中,绝不可能只是谈文论艺,像郑苹如“刺丁案”,这种爆炸性且具有香艳性话题,胡兰成自会向张爱玲说起,加之他曾是“魔窟七十六号”的座上宾,与李士群多有交往,更是位“内幕”的知情者,以胡兰成名士的个性,断无不卖弄此话题者。
(6)
而张爱玲之拒绝承认这材料得之于胡兰成者,乃由于后来胡兰成对她感情的背叛,深深伤害到张爱玲,从此“胡兰成”三个字,似乎在张爱玲的记忆中清除。所谓“最是伤心终无言”,胡兰成对张爱玲的伤害,正如曼桢在《半生缘》中的感受——“不管别人对她怎么坏,就连她自己的姊姊,自己的母亲,都还没有世钧这样的使她伤心”。在当时张爱玲的心境恐怕是“不管别人对她怎么坏,就连她自己的父亲,自己的母亲,都还没有胡兰成这样的使她伤心”。因此即使最亲近的友朋如宋淇者,都避谈胡兰成的事,在张爱玲面前,胡兰成是谈话的禁区。也因此张爱玲没提及材料得之于胡兰成,实不愿再触及情伤。另外若因提及胡兰成将会再度招致“汉奸”污名的攻讦,更是她深深引以为戒的。
而对于张爱玲强调的要将它“当小说读”,学者余斌有一番解读,他说:“《传奇》中人物均为普通人,张身边的人知道底细,固然对辨出‘真身’怀有浓厚兴趣,一般读者难于索隐其间的对应关系,即便能够对号入座,这索隐趣味也只是读小说的余兴,小说固还是小说。《色·戒》则不同,事关重大事件,对应关系太过明显,读者更容易买椟还珠,还原的兴趣超过其他,而一经还原,又以为作者底牌,尽在于此,终是将小说作了野史对待……《色·戒》与‘本事’之间的关系显然复杂得多,说面目全非也许夸张,至少就人物论,是面虽未革而已然洗心。抱负如此,用力如此,张爱玲当然希望读者专注小说本身,拒绝读者将《色·戒》‘还原’为野史、黑幕(真正用心的作家谁不希望读者以自己所期待的方式对待自家作品),倘若由还原的冲动引出政治化的索引或对她个人隐情的究诘(比如由易先生联想到胡兰成),则她更不能容忍。拒绝还原的办法有多种,彻底斩断小说与本事间的联系也许最干脆,是故张爱玲推得一干二净。”( 余斌《〈色·戒〉考》,《万象》杂志,2005年9月)
由于题材的特殊,由于自身身份的敏感,由于曾被攻讦打压的过往,由于要重新解构原本是特工暗杀事件为男女情欲的“张爱玲式的戏码”,张爱玲大费周章地“改写”这个故事,一遍又一遍,“一点都不觉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