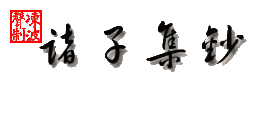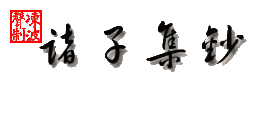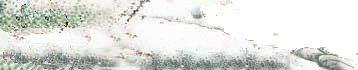傳語曰:聖人憂事,深思事勤,疑當作“勤事”,與“深思”語氣相類。道虛篇云:“憂職勤事。”臧琳經義雜記十八引此文改作“
深思勤事”,是也。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臘,舜若腒;桀、紂之君,垂腴尺餘”。意林引屍子:“堯瘦舜黑,皆為民也。”文子自然篇:“堯瘦□,舜黧黑。”呂氏春秋貴生篇注:“堯、舜、禹、湯之治天下,黧黑瘦瘠。”淮南修務篇引傳曰:“堯瘦臞,舜黴黑,則憂勞百姓甚矣。”荀子非相篇:“桀、紂長巨姣美。”楚辭天問:“受平脅曼膚,何以肥之?”王注:“紂為無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當懷憂□瘦,而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說文肉部:“腴,腹下肥者。” 餘注道虛篇。
夫言聖人憂世念人,“念人”當作“念民”,蓋唐人諱改,而今本沿之。身體羸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臘與腒,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
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韓非子難二:“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于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又見呂氏春秋任數篇、新序雜事四。桓公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得禹、契不難。舜典:“舜曰:禹作司空,契作司徒。”淮南修務訓:“ 堯治天下,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史記舜紀:“禹、契,自堯時,皆舉用。”故此云堯、舜得之。夫易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臞。說文:“臞,少肉也。”
舜承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 假”音“格”,至也。周語上:“戎狄荒服。”注:“ 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 ”堯尚有憂,舜安能無事。“能 ”猶“而”也。見釋詞。盼遂案:“能”當作“而”,語助詞也。後人因論衡文字中常用“而”為“能”,往往改還本字,不悉此處之“而”用為連詞,又誤解堯尚有憂,至舜更不容無事,遂徑改之,而與下文“上帝引逸,謂虞舜也”及“舜恭己無為而天下治”諸語全相抵牾矣。故經曰:“
上帝引逸。”尚書多士文。“逸” 當作“佚”。漢石經大傳“無逸”作“毋佚”,今文作 “佚”也。自然篇引經正作“佚”,是其證。今本蓋淺人依偽孔本妄改。路史後紀十一注,引此文作“俛”,即“佚”之訛。若作“逸”,則不得訛為“俛”,是所據本尚作“佚”。偽孔傳:“上天欲民長逸樂。”此文指舜,今文說也。江聲、王鳴盛並謂經傳凡言“上帝” 皆指天帝,王充說誤。趙坦寶甓齋劄記謂以上帝為虞舜,未知何本。按:春秋說題辭(御覽六○九。)云:“ 上帝,謂二帝三王。”是亦以“上帝”指虞舜。蓋今文舊說,仲任因之。爾雅釋詁:“引,長也。”高誘注呂覽云:“逸,不勞也。”“逸”、“佚”字通。任賢使能,故長佚不勞。謂虞舜也。盼遂案:尚書多士:“周公曰:‘我聞曰上帝引逸。'” 孔傳曰:“天欲民長逸乎?”是上帝謂天帝也。古經傳凡言上帝,皆指天說,此今古文家所同。然仲任于此以為虞舜,殆於失考。自然篇又云:“上帝,謂舜、禹也。”所失益甚。詳後。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見論語泰伯篇。巍巍者,高大之稱也。“與”,舊說有四。一、“與求”。集解:“
美舜、禹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也。 ”二、“與見”。皇疏引王弼、江熙說:“孔子歎己不預見舜、禹之時。”三、“與益”。孟子滕文公下趙注:“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四、“與及”。孟子孫奭疏:“ 天下之事,未嘗自與及焉。以其急於得人而輔之,所以但無為而享之,不必自與及焉。”孫說與仲任義合。後自然篇引論語,說同。漢書王莽傳上:“莽與專斷,乃風公卿奏言:‘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 ‘今眾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故選忠賢,立四輔,群下勸職,以永康寧。孔子曰云云。'”師古注: “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與讀曰豫。”正與仲任義同,蓋漢儒舊說也。孟子云:“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引孔子曰云云。與齊桓公所云“未得仲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義甚相近。是“不與”,正謂既得禹、皋陶,己不親與其事。趙氏謂舜德莫之“與益”,殊失其旨。孫疏謂“不自與及”,蓋亦不然趙說。夫 “不與”尚謂之臞若腒,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棲棲,論語憲問篇,微生畝曰:“丘何為是棲棲者與?”邢疏: “東西南北棲棲皇皇。”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跛附,盼遂案:“跛” 疑為“皮”之誤。“皮附”與“骨立”對文。僵僕道路乎?“附”,疑當作“跗”。
紂為長夜之飲,糟丘酒池,注見下。沉湎於酒,不舍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尚書無逸:“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小雅常棣釋文:“ ‘湛'又作‘耽'。韓詩云:‘樂之甚也。'”“湛” 、“耽”字通。“之從”作“是從”,漢書鄭崇傳、中論夭壽篇同。“自時厥後”作“時”,鄭崇傳、後漢書荀爽傳同。“或”作“有”,鄭崇傳同。皆今文尚書也。陳壽祺曰:“今文多以訓詁改古文。”漢書杜欽傳: “引經曰:‘或四三年。'言失欲之害生也。”“失” 讀作“佚”,謂逸欲害生,與仲任義同。魏公子無忌為長夜之飲,困毒而死。史記信陵君傳:“公子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紂雖未死,宜羸臞矣。然桀、紂同行,則宜同病,言其腴垂過尺餘,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
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撫梁易柱。”帝王世紀曰:“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史記殷本紀正義引。)引鉤申索,握鐵流湯。”(路史發揮六引。)淮南主術篇:“桀之力,制觡,伸鉤,索鐵,歙金。” 高注:“索,絞也。”蓋紂、桀並以力聞,故所傳異辭。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 史記秦本紀:“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屍子:“飛廉、惡來力角虎兕,手搏熊犀。”(御覽三八六引。)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
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荀子議兵篇:“武王伐紂,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故兵不血刃。”說苑指武篇:“戰不血刃,湯、武之兵。” 桓譚新論:“武王伐紂,兵不血刃,而天下定。”(御覽三二九。)
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為武王所擒,殷本紀言紂自焚,死後,武王斬其頭,非擒也。荀子儒效篇:“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是亦不言擒。淮南主術篇言武王擒紂於牧野,與此合。時亦宜殺傷十百人。今言“
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 屍子:“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頭,手汙於血,不盥(荀子仲尼篇注引誤作“溫”,從謝校改。)而食。”正與“不血刃”之說相反。
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烏之佑,注初稟篇。高祖有斷大蛇、老嫗哭于道之瑞。注吉驗篇。武王有八百諸侯之助,太誓:“遂至孟津,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
依孫星衍輯。)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事具史記本紀。武王之相,望羊而已;骨相篇作“望陽”,字通。說見彼篇。高祖之相,龍顏、隆准、項紫、美須髯、身有七十二黑子。項紫,史、漢並未見,可補史缺。餘注骨相篇。高祖又逃呂後於澤中,呂後輒見上有云氣之驗;注吉驗篇。武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于魚烏,天下義兵並來會漢,助彊于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畔讀叛。宜多於殷。案高祖伐秦,還破項羽,戰場流血,暴屍萬數,後漢書光武紀注:“數過於萬,故以萬為數。”失軍亡眾,幾死一再,盼遂案:“一再”,言非一也。猶公羊所謂“不一而足” 也。儒增篇:“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意與此同。然後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
案周取殷之時,太公陰謀之書,漢志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沈欽韓疏證曰:“謀即太公之陰謀。”國策秦策:“蘇秦得太公之陰符,伏而讀之。”史記:“秦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陰符蓋即陰謀。淮南子要略篇:“
太公之謀。”注:“陰符兵謀。” 食小兒丹,“丹”上恢國篇有“ 以”字。教云(亡)“殷〔亡〕”。“ 亡殷”當作“殷亡”。恢國篇作“教言殷亡”,又云“ 及言殷亡”,並其證。兵到牧野,晨舉脂燭。說苑權謀篇:“武王伐紂,晨舉脂燭,過水折舟,示無反志。”(“
晨舉”句,今本脫,據書抄十三引。)盼遂案:唐蘭云:“四語為太公陰謀中文,嚴輯陰謀失載。”察武成之篇,書序曰:“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書疏引鄭玄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孟子盡心下趙注:“武成,逸書之篇名。”漢志班注:“尚書五十七篇。”師古注引鄭玄敘贊曰:“後又亡其一,故五十七。”所亡,即指武成。班書作于顯宗時,故武成已亡。此云“察武成之篇”,是仲任尚及見之,蓋亡于建武之末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為五十八篇。”是武成尚存。譚死于中元元年,在建武后,仲任于時已三十,宜讀武成矣。趙坦謂本孟子,非也。牧野之戰,牧誓偽孔傳:“紂近郊三十裏地名牧。”疏引皇甫謐曰:“在朝歌南七十裏。”按:說文作 “坶”,云:“朝歌南七十裏。”史殷紀集解引鄭曰: “紂南郊地名。”偽孔傳不足據。“血流浮杵”,赤地千里。偽武成曰:“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賈子新書益壤篇、制不言篇,孟子盡心篇趙注並有“血流漂杵”之文。本書藝增、恢國並作“浮杵”。蓋今文作“浮”,古文作“漂”。吳曰:“‘漂'、‘浮'聲近,宵幽相通轉。”其說是也。如“率肆矜爾”,今文作“率夷憐爾”,正其比。今文多以聲音訓詁易古文也。閻氏尚書古文疏證八,據孟子,謂當日書辭僅“血流杵”三字,訛古文緣趙岐注增“漂”字。其說恐非。若作“血流杵”,仲任無緣著一“浮”字也。吳曰:“赤地千里”,據下文及藝增篇,知非武成原語,乃仲任形頌浮杵之文。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
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
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史記范睢傳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賁,注累害篇。並古勇士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則是三皇、五帝之屬也。各本作“是則”,今從朱校元本正。與上句法一律。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朱校元本“ 頓”作“賴”。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
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篇子貢語。齊世篇引亦云孔子。漢人有此例。說見命祿篇。“若”,論語作“如”。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 ”見孟子盡心下。“策”,宋本作“筴 ”,字同,並為“冊”之借字。曲禮釋文曰:“筴,編簡也。”“耳”,孟子作“而已矣”。“伐”下有“至 ”字。“如”作“而”,“浮”作“流”。崇文本作“ 流”,蓋依孟子改之。李賡芸炳燭編曰:“古‘如'、 ‘而'字通。‘浮'字之誼,似長於‘
流'。又藝增篇、恢國篇俱云:‘ 武成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若孔子言,殆沮浮杵;孫曰:“沮”字無義,當作“ 且”,蓋涉“
浮”字而誤加水旁。本書多“殆且 ”連文。指瑞篇:“殆且有解編發、削左衽、襲冠帶而蒙化焉。”漢書終軍傳作“殆將”。感類篇:“
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恢國篇:“以武成言之,食小兒以丹,晨舉脂燭,殆且然矣。”並“殆且”連文之證。此謂如孔子所言,殆將浮杵矣。故下文辨之云“浮杵過其實”也。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
紂之惡不若王莽。鄒伯奇曰:“ 桀、紂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見感類篇。)紂殺比干,莽鴆平帝;漢書翟義傳:“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平帝紀,師古曰:“漢注云:‘帝春秋益壯,以母衛大後故怨不悅。莽自知益疏,篡弑之謀由是生。因到臘日,上椒酒,置藥酒中。'”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主隆於誅臣,嗣立順於盜位,士眾所畔,宜甚於紂。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台,血流沒趾。後漢光武紀:“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圍昆陽數十重,矢如雨下,城中負戶而汲。”劉玄傳:“長安中兵起,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台,收璽綬傳首詣宛。”注:“漸台,太液池中台也。為水所漸潤,故以為名。”按:漢書郊祀志:“漸台高二十餘丈,在建章宮北。”而獨謂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舊本段。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鐘,孔子百觚。”孔叢子儒服篇,平原君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鐘,孔子百觚。”環氏吳紀:“孫皓問張尚曰:‘孤飲酒可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
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 因此發怒收尚。”(三國志吳志張紘傳注。)傅玄敘酒賦:“唐堯千鐘竭,周文百斛泊。”(書抄一四六。)後漢書孔融傳注引融集與曹操書曰:“堯不千鐘,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張璠漢記:“孔融曰:‘堯不飲千鐘,無以成甚聖。'”(魏志崔琰傳注引。)抱撲子袪惑篇:“堯為人長大,美髭髯,飲酒一日中二斛余,世人因加云千鐘,實不能也。”或云堯、舜,或云周文、孔子,主名不定,殊難征信。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
如一坐千鐘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說具下文。〔
聖人〕胸腹小大,與人均等,“聖人”二字舊脫,語無主詞,“與人均等”句,於義失所較矣。下文云:“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是其義。今據御覽八四五引增。飲酒用千鐘,用肴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孫曰:御覽七六一引作“若酒用千鐘,則肉宜用百牛;酒用百觚,則肴宜用千羊。”意較完足,疑今本有脫誤。暉按:孫說非。御覽八四五引作“若飲千鐘,宜食百牛;能飲百觚,則能食十羊”,與前引又有出入。蓋以意增,非今本脫誤。“百觚”上省“飲酒用”三字,“用” 下省“肴”字。平列句,得蒙上句省也。夫以千鐘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魯語下:“防風氏,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韋注: “防風,汪芒氏君之名。骨一節,其長專車,計之三丈。”家語辨物篇王注、(史孔子世家集解引今本脫。)述異記並云長三丈。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洪範五行傳:“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御覽三七七。)谷梁文十一年傳注,謂“長五丈四尺”。疏引春秋考異郵云:“長百尺。”公羊何注同。左氏杜注:“ 蓋長三丈。”按:魯語下曰:“防風于周為長狄。僬僥長三尺,短之至。長者不過十之,(“之”字今本脫。家語、說苑辨物篇誤同。此從孔子世家、左傳疏補。)數之極也。”是言長狄十倍僬僥之長。杜蓋據以為說。博物志曰:“長五丈四尺。或長十丈。”兼存公羊、谷梁說也。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眾多,是缺文王之廣,貶孔子之崇也。
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尚書酒誥篇,周公誥康叔,述文王之詞。孔傳:“文王朝夕敕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鐘,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朱校元本作“教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
且千鐘之效,百觚之驗,何所用哉?“ 所”,宋本、朱校元本同。程、王、崇文本並作“時” 。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不能厭飽。 晉語二韋注:“福,胙肉也。”左僖四年傳杜注:“胙,祭之酒肉。”因饗射之用酒乎? 孫曰:此與上“因祭用酒乎”文例正同,不當有“之”字,蓋衍文。暉按:孫說疑非。本書駢列語,後列每加一語詞。道虛篇:“物生也色青,人之少也發黑。”上文云:“
若孔子言,殆且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後列並多一“之”字,與此文例正同。 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朱校元本“觴”作“觚”。下同。禮記玉藻:“君若賜之爵,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左宣二年傳:“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過於三觴,醉酗生亂。鄭玄曰:“禮飲過三爵,則敬殺。”說文:“□,酒醟也。”經典多作“酗”。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酗亂盼遂案:“亂” 上依上文當有“生”字。身,自用酒千鐘百觚,大之則為桀、紂,小之則為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朱校元本“用”作“又”。
世聞“德將毋醉”之言,書酒誥:“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今文“無”作“毋 ”。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為千鐘,空益孔子以百觚矣。“為”字於義無取,兩句文例正同。蓋衍文。舊本段。
傳語曰:“紂沈湎於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為長夜之飲,亡其甲子。”此事有二說。韓詩外傳二:“桀為酒池糟堤,牛飲者三千。”又卷四:“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裏,而牛飲者三千人。”新序刺奢篇、節士篇略同。並謂桀事也。韓非子喻老篇:“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呂氏春秋過理篇:“糟丘酒池,肉圃為格,刑鬼侯之女,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淮南本經訓: “紂為肉圃酒池。”六韜:“紂為君,以酒為池,回船糟丘,而牛飲者三千人。”(今本脫。書抄一四六引。)賈子新書:“紂糟丘酒池。”(今脫,書抄二0引。)說苑反質篇:“紂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並以為紂事也。史記殷本紀從後說。屍子:“桀、紂縱欲長樂,以苦百姓,六馬登糟丘,方舟泛酒池。”(御覽六七八。)又屬之兩人。主名不定,明其事非實也。路史發揮六曰:“桀、紂之事,多出模仿,紂如是,桀亦如是,豈俱然哉?”可謂有史識矣。淮南本經篇注:“紂積肉以為園圃,積酒以為淵池。今河內朝歌,紂所都也,城西有糟丘酒池處是也。”史記殷本紀正義:“括地志云:‘酒池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三裏。'”新序刺奢篇:“ 紂飲酒七日七夜。”楚詞王逸九思注:“紂為九旬之飲而不聽政。”書抄二一引世紀:“紂飲七日,不知歷數。”“沈湎于酒”,尚書微子篇文。湎作“酗”。此今文經也。沈之為言淫也。說文:“湎,沈於酒也。”淮南要略注:“沉湎,淫酒也。”
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為樂。令酒池在中庭乎?金鶚求古錄曰:“
凡言庭,皆廟寢堂下。”中庭東西,為群臣列位,聘燕宜其處,故據以言。則不當言為長夜之飲。坐在深室之中,閉窗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之,至也。乃複還坐,則是煩苦相踖藉,釋名釋姿容:“踖,藉也。以足藉也。”後漢明帝紀注引五經要義:“籍,蹈也。”眾經音義九引字林:“躤,踐也。”“藉”、“籍”、“躤”音義並通。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盼遂案:“前”字疑涉下文多“前”字而衍。下“臨池而坐”句可證。俛飲池酒,〔後〕仰食肴膳,“ 仰”上當有“後”字。池酒在前,肴膳必陳於後。下文 “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於肴膳”,即謂肴膳在坐後,不便也。且“前飲”連文,則此當以“前俛飲池酒” 為句。“後仰食肴膳”,句法正相一律。蓋後人不審其義,以“前”字屬上讀,而妄刪“後”字。倡樂在前,乃為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於肴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
夫飲食既不以禮,臨池牛飲,則其啖肴不復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舊本段。
傳又言:“紂懸肉以為林,令男女□而相逐其間。”史記殷本紀文。公孫尼子謂“紂為肉圃”。(初學記。)三輔故事謂為肉林。(
書抄二0。)餘已注前。是為醉樂淫戲無節度也。“為”讀作“謂” ,與上“欲言”、“此言”文例同。
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潔不辱。廣雅釋詁:“辱,汙也。”今言男女□相逐其間,何等潔者?盼遂案:“何等潔者”,言不潔也,此漢人語法。藝增篇“何等賢者”,言不賢也; “堯何等力”,言無力也,皆與此一例。如以醉而不計潔辱,則當其(共)浴於酒中。孫曰:“其”字當從元本作“共”。(崇文本作“共”,蓋亦據別本改。)而□相逐於肉間,何為不肯浴於酒中?“而”讀作“能”。以不言浴於酒,知不□相逐於肉間。
傳者之說,或言:書抄、四五引作“傳者說”。“車行酒,騎行炙,盼遂案:悼廠云:“惠氏後漢書補注云:‘古人以車騎行酒肉。馬融廣成頌云“清醪車湊,燔炙騎將”,亦其例也。'”百二十日為一夜。”出太公六韜。又見世紀、三輔故事。(書抄二0引。)盼遂案:“夜”下當有“亡其甲子”一句,今脫,則下文兩言“亡其甲子”之語無稽。
夫言“用酒為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為林”,即言“騎行炙”非也。“ 即”猶“則”也。
或時意林、御覽八四五並引作“ 或是”。紂沈湎,謂□醟也。覆酒,滂□於地,元本作“滂沱”。朱校同。意林、御覽引亦並作“沱”。“它”、“也”二字自異,而從“它”從“也”之字多亂。此當作“沱”為正。即言以酒為池;釀酒糟積聚,意林、御覽引並作“釀酒積糟”。則言糟為丘;懸肉以(似)林,“以”,元本作“似”。朱校同。御覽引亦作“似”。當據正。則言肉為林;林中幽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其逐;或時載酒用鹿車,風俗通(御覽七百七十五、後漢書趙□傳注引。)曰:“俗說鹿車窄小,載(一作“裁 ”。)容一鹿也。或云樂車。乘牛馬者,銼斬飲飼達曙;今乘此,雖為勞極,然入傳舍,偃臥無憂,故曰樂車。無牛馬而能行者,獨一人所致耳。”後漢書趙□傳曰:“載以鹿車,身自推之。”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史記衛世家:“封康叔為衛君,周公申告曰:‘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誥:“嗣王酣身,惟荒腆於酒。 ”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酒池,懸肉為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舊本段。
傳言曰:“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于酒池。”此復述上文,非另引傳也。夫夏官百,殷二百,週三百。禮記明堂位文。鄭注:“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週三百六十官也。昏義,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以夏、周推之,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按:荀子正論篇又云:“古者天子千官。”蓋都不足據也。紂之所與相樂,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書家欲惡紂,故言三千人,增其實也。舊本段。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尚書大傳、荀子堯問篇、韓詩外傳三、說苑尊賢篇並有此文。贄,禽贄,所執以為禮也。白屋,謂庶人以白茅覆屋者也。謂候之也。盼遂案:吳承仕曰:“曲禮‘使某羞',鄭注:‘羞,進也,言進於客。古者謂候為進。'正義曰:‘古者謂迎客為進,漢時謂迎客為候。'據此,則候謂漢時通語。此云‘謂候之',亦以漢語比古事,與鄭同意。”
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貞幹也;五行志:“鼎三足,三公象。”易鼎卦九五:“鼎折足。 ”李鼎祚引九家易曰:“鼎者,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也。”周官乙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鄭志答趙商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于成王。”“貞”通“ 楨”,楨亦幹也,並築具。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
(時)或〔時〕待士卑恭,“時或”當作“或時”,與下“或時”平列,本書常語也。 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 秦策注:“起猶舉也。”以璧迎禮之,“璧”,舊校曰:一本作“圭” 。暉按:“璧”是,一本作“圭”,非。公羊定八年傳何注:“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眾,璋以徵召。”白虎通瑞贄篇云:“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並謂璧以聘問,則此云“以璧迎禮之”是也。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舊本段。
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斫。 ”太史公自序引墨家言。又見史記始皇紀引韓子。文選東京賦注引墨子、韓非子五蠹篇、淮南主術篇、史記李斯傳、帝王世紀(御覽八0。)並只謂堯事。史記自序正義:“屋蓋曰茨,以茅覆屋。”索隱韋昭云:“采椽,櫟榱也。”
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剪不斫,增之也。
經曰:“弼成五服。”尚書皋陶謨文。今見偽孔本益稷篇。五服,五采服也。段玉裁曰:“此今文書說也。”暉按:皋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益稷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今文說以五服為五章,廣雅曰:“山龍,彰也。”即舉山龍以該五章。五章即大傳所舉五采,故云“五服,五采服” 。考馬、鄭注,並謂侯、甸、綏、要、荒五服,與仲任說不同。若如仲任說,則經義上下不貫,孫奕、孫星衍謂為誤釋,是也。皮錫瑞曰:“仲任以五服為五采服,不知下文之解若何。若以五服為天子、諸侯、次國、大夫、士五章之服,如後世所云冠帶之國,義亦可通。” 盼遂案:書皋陶謨:“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孔安國、馬融、鄭玄、王肅注,皆即大禹“荒度土功”為說。仲任釋五服為五采服,雖本今文師說,然於經義則遠。 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孫星衍曰: “司馬法云:‘章,夏後氏以日月,尚明也。'則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漢東平王蒼南北郊服議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天王□冕十有二旒,以明天數,旗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續漢輿服志注引東觀書。)是古說以日月為旗章也。大傳亦不言五服畫日月星辰,充說誤也。”暉按:夏本紀云:“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史公云“作文繡服色”,即釋經文“山龍、華蟲”至“作服”也,而“日月星辰” 別出於上者,即史公不以“日月星辰”在文繡服色之中,其義與伏生大傳同。此文謂:“服五采,畫日月星辰。”景知篇:“加五彩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猶絲帛有五色之巧也。”以“日月”與山龍、華蟲並言,則其義亦謂服色有“日月”也。後漢書輿服志曰:“顯宗遂就大業,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又云:“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皮錫瑞曰: “據此,則是歐陽說冕服章數以十二、九、七為節,大、小夏侯說冕服章數天子至公侯以九為節,卿以下以七為節,皆與大傳言五服五章不同,此三家今文之背其師說者。當時三家博士,變今文尚書之師說,以傅會周官,不知周禮非可以解虞書。經明言‘五服五章',不得有十二章、九章、七章之制。鄭玄據周禮以推虞制,其義正本于歐陽、夏侯。仲任云服日月星辰,蓋沿歐陽之誤說,以為天子服有日月星辰也。”茅茨、采椽,非其實也。舊本段。
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史記儒林傳:“秦焚詩書,坑術士。”言燔燒詩書,滅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傳文書之人也。盼遂案:吳承仕曰:“漢人多言五經,遂以貤說舊事,不知漢前實言六經。藝文志‘三十而五經立',其誤亦同。”“皆”當是“盡”之誤字。 “盡挾經傳文書之人”者,將挾經傳文書之人一網而打盡之也。此處“盡”為動詞,踐人不了,以“皆”與“ 盡”同,意改之,而不悟不與下文“盡坑之”一語相照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
言燔燒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台,正說篇作“宮”。史記始皇紀、李斯傳同。儒士七十人前為壽。正說篇作“博士”,與始皇紀合。李斯傳:“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 疑此文當作“博士”,指周青臣輩也。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於越進諫始皇不封子弟功臣正說篇句首有“以為”二字。自為狹(枝)輔,“ 狹”當作“枝”。史記始皇紀作“枝”,李斯傳作“支 ”,可證。宋、程本作“挾”,王本、崇文本作“夾” ,並“枝”字形訛。□周青臣以為面諛。“ □”,“刺”之隸變。毛詩:“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魯詩、石經“刺”作“□”。顏氏家訓書證篇曰:“ ‘刺'應為‘朿',今作‘夾'也。”盼遂案:“□” 為“刺”之俗體。“刺周青臣”,不辭,疑本為“劾” 。劾者,劾告罪人。後訛為“刺”耳。又案:“
狹”,宋本作“挾”,是。說文: “挾,俾持也。”始皇下其議于丞相李斯。李斯非淳於越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說文:“秦謂民為黔首,謂黑色。” 臣請敕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諸刑書)者〔刑〕;“ 諸書”二字,涉“詩書”偽衍。“刑”字當在“者”字下。始皇紀、李斯傳未言刑書。正說篇作“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刑”,是其證。悉詣守尉集(雜)燒之; “集”當從始皇紀作“雜”。“雜”一作“□”,故殘為“集”。元本正作“□”。朱校同。 有敢偶語詩書,棄市;“書”下元本有“者”字。朱校同。始皇紀與今本合。以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弗舉,始皇紀有 “者”字,此蒙上文省。與同罪。”始皇許之。
明年,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為妖言。始皇使禦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始皇紀無“者”字。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始皇紀“七”作“餘”。文選西征賦注引史作“四百六十四人”。疑史文原不作“餘”。唐李亢獨異志云:“二百四十人。”未知何據。皆坑之。史記云:“坑之咸陽。”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史儒林傳正義。)古文奇字、(類聚八0。)獨異志並云“坑於驪山”。盼遂案:“告引者”之“者”,宜依史記改為“有”字,屬下讀。
燔詩書,起淳於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為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欲絕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今從宋本段。
傳語曰:“町町若荊軻之閭。”未知何出。“若”,元本作“者”,朱校同。疑誤。意林引同今本。急就篇顏注:“平地為町。”釋名釋州國曰:“鄭,町也。其地多平,町町然也。”“町町”猶詩東山之“町畽”。說文:“田踐處曰町。”又:“畽,禽獸所踐處。”踐處,則其地夷平也。廣雅釋訓曰:“ □□,盡也。”王念孫曰:“
町町,與□□義同。”盼遂案:“ 町町”,蕩盡之意。廣雅釋訓:“
□□,盡也。”王氏疏證引此文為說。今按:町町、□□聲近義通。言荊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漢書鄒陽傳: “荊軻湛七族。”(“荊”字依王念孫校補。)應劭注:“荊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九族有二說,五經異義:“夏侯、歐陽說: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古尚書說,從高祖自玄孫,皆同姓。”(左桓六年傳疏。)其後恚恨不已,複夷軻之一裏。一裏皆滅,故曰町町。
此言增之也。
夫秦雖無道,無為盡誅荊軻之裏。始皇幸梁山之宮,始皇三十五年。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損車騎。始皇知左右泄其言,莫知為誰,盡捕諸在旁者皆殺之。始皇本紀“諸”下有“時”字,義較長。朱校元本“諸”下有“生”字,疑“時”之誤。其後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始皇三十六年。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 ”紀妖篇、史記始皇本紀、漢五行志“ 地”上並有“而”字,疑此文脫。 〔始〕皇(帝)聞之,“始”字脫,“帝”字涉上文衍。上下文並稱“始皇”,“皇帝”非其義也。紀妖篇、始皇紀並作“始皇聞之”,是其證。盼遂案:依文例當作始皇。此史駁文未盡正者也。令禦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之。紀妖篇“人”上有 “家”字,與始皇紀作“居人”義合。
夫誅從行于梁山宮,及誅石旁人,欲得泄言、刻石者,不能審知,故盡誅之。荊軻之閭,何罪于秦而盡誅之?如刺秦王在閭中,不知為誰,盡誅之,可也;荊軻已死,刺者有人,一裏之民,何為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荊軻刺秦王,見前書虛篇注。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不言盡誅其閭。
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眾多,同裏而處,誅其九族,一裏且盡,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