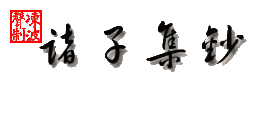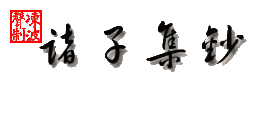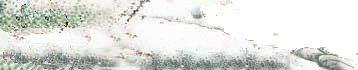藝增篇藝,謂經藝也。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為十,見百益以為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歧道,並注率性篇。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
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吳曰:疑當作“大賢”。盼遂案:“
人賢”二字,當以為“賢人”。上文“小人”,下文“聖人”,皆與此相應。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為,不妄亂誤以少為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
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恍惑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
尚書〔曰〕:依下文例補“曰” 字。“協和萬國。”堯典文。“
邦”作“國”,說見前篇。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並及夷狄也。
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
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內。此今文書說也。王制疏引五經異義曰:“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書虛篇:“舜與堯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談天篇:“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 ”別通篇:“殷、周之地極五千里。”宣漢篇:“周時僅治五千里內。”難歲篇:“九州之內五千里。”又御覽六二六引孫武曰:“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並今文說也。今文家不以為實有萬國,故不以為實有萬里也。周時諸侯千七百九(七)十三國,“ 九”當作“七”,尚書大傳洛誥傳:“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于周,退見文、武屍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王制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鄭注:“周因殷諸侯之數。”並其證。荒服、戎服、要服周禮夏官職方氏注:“服,服事天子也。”周語上:“夷蠻要服,戎狄荒服。”韋注: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也。荒,荒忽無常之言也。”禹貢、周禮、周語,並無“ 戎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注感虛篇。若穿胸、儋(耴)耳、僬僥、跋(跂)踵之輩,淮南地形訓有穿胸民,高注:“ 穿胸,胸前穿孔達背,南方國名。”海外南經曰:“貫胸國,人胸有竅。”竹書紀年有貫胸氏。博物志二曰: “穿胸國,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到,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禦之,行城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氏之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使,怒而射之,迅風雷雨,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為穿胸民。”括地圖文略同。方以智曰:“ 儋耳”即“耽耳”。淮南曰:“耽耳在北方。”漢南海有儋耳郡,注:“作聸,大耳。”說文:“耳曼無輪廓曰聃。”老聃以此名。子長疑太史儋即老聃。則“儋” 、“聸”、“聃”一字。今儋州即儋耳。淮南“在北方 ”,或訛舉,或同名乎?暉按:方說非也。漢之儋耳郡,唐之儋州,地在南方,與此無涉。說文明言南方有儋耳國。此“儋耳”在四海之外,本海外北經、淮南地形訓。“儋”當作“耴”,初訛為“耽”,再轉為“聸” 、為“儋”耳。(段玉裁曰:“古作耽。一變為聸,再變為儋。”)今淮南地形訓“耴耳”偽作“耽耳”。(依王念孫校。)此則由“耽”轉寫作“儋”也。呂氏春秋任數篇:“北懷儋耳。”高注:“北極之國。”則“ 儋”亦當作“耴”,與此誤同。(大荒北經:“儋耳之國,任姓。”亦“耴耳”之誤。)淮南高注:“耴耳,耳垂在肩上。耴讀褶衣之‘褶',或作‘攝',以兩手攝耳居海中。”海外北經曰:“聶耳之國,在無腸國東,為人兩手聶其耳,縣居海水中。”王念孫曰:“耴耳即聶耳。”魯語下:“焦僥民,(今作“僬僥氏”,從段玉裁校。)長三尺,短之至也。”韋注:“僬僥,西南蠻之別名也。”(今脫“名”字,從孔子世家集解補。)海外南經曰:“焦僥國在三首國東。”括地志曰: “在大秦國北。”大荒南經云:“幾姓。”先孫曰:“ 跋踵”當作“跂踵”。山海經海外北經:“跂踵國在拘纓東。”(郭注引孝經鉤命決云:“焦僥、跂踵,重譯款塞。”)暉按:孫說是也。山海經郭璞注:“跂音企。”是“跂”讀“企”。企,舉踵望也。淮南地形訓高注:“跂踵,踵不至地,以五指行。”大荒北經郭注: “其人行,腳跟不著地也。”字又作“歧”。竹書:“ 歧踵戎來賓。”呂氏春秋當染篇:“夏桀染于幹辛、歧踵戎。”山海經曰:“流沙行五百里有山,曰跂踵山。 ”或即跂踵國地。併合其數,不能三千。“ 能”猶“及”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褒增過實,以美堯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眾,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 萬國”。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
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曰‘ 協和萬國',此之謂也。”據此,則今文說以萬國為實數,非虛增也。仲任以為褒增,與之異者,皮錫瑞曰: “仲任歐陽說,與班固夏侯說不同。”其說是也。孫奕示兒編十三,以仲任謂唐無萬國為誤經義,非也。猶詩言“子孫千億”矣,見大雅假樂篇。 美周宣王之德,陳喬樅魯詩遺說考:“毛詩以假樂之詩為嘉成王。今據論衡述詩,以為美周宣王之德,是魯詩之說與毛義異。”能慎天地,“慎”,舊校曰:一作“順”。暉按:“慎”讀作“順”,聲近字通。天地祚之,子孫眾多,至於千億。鄭箋:“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是非謂子孫之數有千億也。與王說異。言子孫眾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夫子孫雖眾,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案後稷始受邰封,大雅生民曰:“有邰家室。”毛傳:“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後稷,故國後稷于邰。”訖于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內屬,血脈所連,不能千億。“ 不能”猶“未及”也。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眾多,吳曰:“萬”字疑誤。暉按:“萬言眾多”,猶言“千萬之為言眾多也 ”,舉“萬”以胲“千”。故尚書言“
萬國”,詩言“千億”。
詩云:“鶴鳴九皋,聲聞於天。”見小雅鶴鳴。今本“鳴”下有“於”字,因唐石經誤也。古書引詩,皆無“於”字。詳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段玉裁毛詩故訓傳、錢大昕養新錄、李富孫詩經異文釋、李賡芸炳燭編。盧文弨龍城劄記曰:“‘皋'一作‘ 皋',當作‘
□',即古‘澤'字。”李賡芸曰:“太玄上次五:‘鳴鶴升自深澤。'範望注,詩云: ‘鶴鳴九皋,聲聞於天。'據此,‘九皋'當作‘九澤 '。說文‘□'古文以為‘澤'字。毛詩必本作‘□' ,字與‘皋'相似,因而致訛。”暉按:鄭箋:“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楚詞湘君王注:“澤曲曰皋。” 若作“□”,即“澤”字,則鄭、王不容別其義於“澤 ”也。盧、李說恐非。言鶴鳴九折之澤,此韓詩說也。見釋文。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韓詩外傳七曰:“ 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下引此詩,義與此說相近。荀子儒效篇:“君子隱而顯,微而明。” 漢書東方朔傳:“苟能修身,何患不榮。”並引此詩。毛傳、鄭箋義同。蓋詩今古文說無異也。
〔言〕其聞高遠,可矣;“其” 上當有“言”字,與下“言”字平列。本篇文例可證。盼遂案:“其”上應有“言”字。上文“言子孫眾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下文“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與此文法一律。言其聞於天,增之也。
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云中,從地聽之,言從地能聞之。度其聲鳴於地,當複聞於天也。夫鶴鳴云中,人聞聲仰而視之,目見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裏,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御覽九一六引作:“按鶴鳴參天,人則不聞。鳴在於澤云何謂乎?” 蓋意引之,非此文有脫誤也。何則?天之去人以萬數遠,“萬數”,以萬為數也,漢人常語。仲任以為天地相去,六萬餘裏。見談天、說日篇。 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於地,當複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云中,人從下聞之;如鳴於九皋,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上也?無以知,意從准況之也。盼遂案:“意”系“竟”之誤字。
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為然;或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
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孑遺。”見大雅云漢。“維周”毛詩作“周餘”。王應麟詩考三以為異文,李富孫曰:“治期篇仍作‘周餘'。孟子引詩同,則此作‘維周',當為駁文。”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皇甫謐曰:“宣王元年,不藉千畝,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 ”(云漢序疏。)竹書謂二十五年大旱。陳啟源毛詩稽古篇曰:“在宣王初年。”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孑,餘也。見方言、小爾雅。言周眾民未有餘遺一人不被害者。蓋三家詩說。毛傳、孟子萬章上趙注,並云:“孑,孑然。”孔疏:“孑然,孤獨之貌。謂無有孑然得遺漏。”此“孑遺”下有“一人”二字,知非訓“孑”為“ 孑然”,是與毛說異也。孟子謂“無遺民”。按鄭箋謂 “言餓病也”。此文云“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是亦非謂盡死無一人遺餘也,義與鄭同。
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謂無一人不愁痛,非謂無一人。此約舉上文也。增之也。
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扣”讀作“苟”,(淮南精神訓注:“叩,或作□。”眾經音義一引三蒼:“扣作□。”說文:“狗,叩也。從犬,句聲。”是“叩”有“句”聲。)聲近字通。苟,誠也。見論語裏仁篇孔注。若其富人谷食饒足者,廩囷不空,口腹不饑,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謂水患。丘陵之上不湛也。湛,沒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舊本段。
易曰:“豐其屋,豐,大也。蔀其家,虞翻注:“蔀,蔽也。”窺其戶,易作“窺”。淮南泰族篇同此。 “窺”“窺”字通。釋文引李登云:“小視。”□ 其無人也。”“□”,唐石經作“闃” 。宋岳刻本,何休、王逸、范甯引易,並同此。文選吳都賦劉注引虞注:“
□,空也。”惠棟曰:“說文□部:‘閿,低目視也。'‘□'當作‘閿',與‘窺'義合。”文見豐卦上六爻辭。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淮南泰族篇引此經釋之曰:“無人者,非無眾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公羊、莊四年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何注:“
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猶易曰□其無人。”離騷王逸注:“無人,謂無賢人也。易曰:窺其戶,□其無人。”谷梁僖三十一年傳範注:“亡乎人,若曰無賢人也。凱曰:其猶易稱窺其戶,□其無人。” 並與仲任說同也。沈濤曰:“此解‘□其無人',與虞翻、幹寶不同,(集解引。)當是漢易學家承師說,而仲任引之。”其說是也。尚書曰:“毋曠庶官。” 皋陶謨文。曠,空;庶,眾也。毋空眾官,置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偽孔傳:“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太史公說:(史記夏本紀。)“非其人,居其官。”並與仲任說同。
夫不肖者皆懷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嚚身中無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猶,均也。言居官小材,戶中具臣,非狂妄者,均有益也。如何謂之空而無人?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見大雅文王篇。濟濟,朝廷之儀也。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宜言“闃其少人”,尚書宜言 “無少眾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盼遂案:“尤”,訓過,訓非。
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饑。食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言扶持病人。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省一“杖”字。或操竹杖,皆謂不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易持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盼遂案:吳承仕曰:“持字誤。”“持”字涉上文“把持”字而衍。“其”字因與“具”字形近而衍。此文本是“易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眾官,亦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舊本段。
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泰伯篇集解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傳曰:“ 有年五十擊壤于路者,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堯”下當有“之”字。感虛、須頌並有。下“大哉!堯之德乎”,即復述此文。是其切證。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論語考比讖、(御覽八二二。)逸士傳(海錄碎事十七。)並見此事。擊壤注刺孟篇。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
言蕩蕩,可也;乃(欲)言民無能名,增之也。 “欲”,涉下文“欲言民無能名”而衍。此謂論語云“民無能名”,是增之也。“欲”字於義無取。“言某某,可也;而言某某,增之也。”三增文例並同,可證。盼遂案:“欲”字當在“此”字下,即此欲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
四海之大,萬民之眾,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
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注見率性篇。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為人父,為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為君子,人有禮義,孫曰:“為”當作“有”,蓋涉上文 “為人父”而誤。上云:“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治期篇云:“世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並其證。暉按:孫說非也。 “為”即“有”也。孟子滕文公篇:“夫滕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趙注:“為,有也。”上言“為”,下言“有”,互文也,不煩改字。父不失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
年五十擊壤于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為伍,何等賢者?子路使子羔為郈宰,先孫曰:論語先進篇“郈”作“費”。史記弟子列傳作“使子羔為費、郈宰”。疑齊古論語有作“郈”者,與今本異也。讀書叢錄曰:左定十二年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子路使子羔,當在此時。或費,或郈,權一使之。故史記並書之。銅熨斗齋隨筆曰:史記弟子傳“費”字衍文。蓋古本論語作“郈宰”,不作“費宰”。論衡藝增篇作“郈宰”,可見漢以前本皆如是。問孔篇仍作“費宰”,乃後人據今本論語改。史記正義引括地志:“鄆州宿縣二十三裏郈亭。 ”張氏但釋“郈”,不釋“費”,可見所據本尚無“費 ”字。暉按:論衡確本作“郈”。問孔、量知、正說並作“費”,乃所引論語明文,淺者得以據改也。史記亦只作“郈”,沈說足征。考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處地自異。公羊定十年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左氏、谷梁“費”並作“郈”,與此相同。未明何說。孔子以為不可,未學,無所知也。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注: “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
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蕩蕩不能名,則臣不知君,故不可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盼遂案:吳承仕曰:“
議讓當是譏讓,形近而誤。”而無知之。“讓”字疑涉“壤”字衍,又因“議”字“言”旁而誤。“不能議”與“不能述”,文正相對。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舊本段。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今我民罔不欲喪。' ”見西伯戡黎。“不”作“弗”。段玉裁、孫星衍並云:今文作“不”。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
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
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江聲謂:惡臣安於紂恩。若民則不堪虐政,實無不欲王亡。祖伊固言民,不言臣也。以為增語,非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蓋傳語。所出未聞。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警悟也。“其” ,程本作“可”。“警,宋本作“語”。朱校同。蘇秦說齊王曰:齊宣王。“臨災之中,齊策一、史記蘇秦傳並作“塗”。臨災,齊都。車轂擊,人肩摩,高誘曰:“擊,相當。摩,相摩。”舉袖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高曰:“揮,振也。言人眾多。”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
之說齊王”,朱校元本作“增語激齊”。
賢聖增文,外有所為,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
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助紂也。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盼遂案:此十四字疑衍。
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頓,傷也。輒燥入土,安得杵浮?程本作“浮杵”,疑是。宋本、朱校元本同此。且周、殷士卒,皆□盛糧,(或作乾糧)先孫曰:此四字當是宋人校語,誤入正文。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 孟子盡心下趙注,偽武成孔注,並謂“ 杵”為“舂杵”,與王義同。蓋舊說也,故據以立論。惠士奇禮說曰:“司馬法云:(見周禮地官鄉師注。) ‘輦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加二版二築。'築者,杵頭鐵遝也,以築壘壁,故武成有浮杵語。”杵是築杵,則非舂用也。
言血流杵,“杵”上當有“浮” 字。仲任釋經,謂血流至於浮杵,非若孟子謂杵被血流動也。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 惟”,宋本、朱校元本並作“雖”。故至浮杵。此明賢聖增文,外有所為也。舊本段。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霣如雨”。三傳“夜”下無“中” 字。“星霣”上有“夜中”二字。後說日篇兩引,並與此同。盼遂案:吳承仕曰:“左氏義讀如雨為而雨,疑公羊說是。”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
如雨'?盼遂案:“如”字衍。公羊無。不脩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複。'孫曰:此文不當有“如”字。蓋涉上文“如雨”而衍。說日篇及公羊莊七年傳並無“如” 字。當據刪。楊曰:“而”當為“如”字讀。暉按:楊說是也。下文:“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如複。 ”是仲任以“如”訓“而”。下文:“星霣不及地,上複在天。”即此“複”字之義。盼遂案:下曰“雨星,不及地尺如複”句,“雨”上即無“如”字。君子脩之〔曰〕:孫曰:“之”下脫“曰” 字,當據說日篇及公羊莊七年傳補。下“孔子脩之”句同。‘
星霣如雨。'”“不脩春秋”者,未脩春秋時魯史記,曰:何休曰:“不脩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說詳謝短篇。“雨星,不及地尺如複。”“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脩之〔曰〕:“星霣如雨。”“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為云,上不及天,下而為(
云)雨。“云”字與上“云”字義複,衍文也。感虛篇曰:“夫云出於丘山,降散則為雨矣。”又曰:“雨凝為雪,皆由云氣。”與此文意同,可證。盼遂案:下“云”字應作“雨”,本書感虛篇“ 夫云氣生於丘山,降散則雨矣”,與此意同。 (星)星隕不及地,上“星”字衍。上複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言脩正之。
夫星霣或時至地,或時不能,“ 不能”猶言“未及”。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 尺”,亦似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 何休曰:“不言尺者,霣則為異,不以尺寸錄之。”仲任謂“尺丈難審”,於義較長。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 ”。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
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 賁光”,書抄六三引作“王賁”。孔廣陶校曰:作“賁光”非。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風俗通正失篇:成帝見劉向以世俗多傳道文帝常居明光宮聽政,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有此事不?向對曰:“皆不然。”王楙野客叢書二一曰:“漢有兩明光宮,按三輔黃圖,一明光宮屬北宮,一明光宮屬甘泉宮。屬北宮者,正成都侯商避暑之所。屬甘泉宮者,乃武帝所造,以求仙者。”暉按:元後傳注,師古引黃圖曰:“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也。”章懷太子亦謂桂宮,明光宮在北。而師古于武帝紀注謂武帝所起者在城內,即成都侯商避暑處。是無屬甘泉與北宮之別。朱珔然其說。然按武帝於太初四年起明光宮,據此文文帝曾居明光宮,則在武帝前已有宮名明光者。若實無,光武不當只辯曰“不居”耳。是明光宮有二,王說可信也。至成都侯所居者何,無以定其說。盼遂案:風俗通義卷二,孝成皇帝問劉向曰:“
孝文皇帝常坐明光宮聽政,斷獄三百人,有此事不?”對曰:“皆不然。”應劭謹案:“ 太宗時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又:“ 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崩未央宮。在時平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殿。”是應說與此有異。太宗,孝文帝;中宗,孝宣帝也。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人。”風俗通正失篇曰:“文帝平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積善脩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夫賁光上書於漢,漢為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為實事也。“而”猶“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