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雷铎:特立独行“士大夫”
作者:陈玉虹
静坐于慕名已久的“白云山房”,品着滚烫醇厚的普洱茶,雷铎先生为我们点燃了一段来自柬埔寨的千年水沉香。话题就从这沉香说起,他讲“运用之妙,存乎手心”,惋惜“我们偏废了些器官,只沉溺于声色之中”,然后再讲历史变迁、民间故事、民俗风尚,不知不觉中,围绕一截时隐时现的沉香,他已经纵横中外古今讲了大半个小时。

简介
雷铎现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一级作家、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其治学,主要为文学、国家和书画三大领域。

文学方面,出版有《男儿女儿踏着硝烟》、《子民们》、《从悬崖到坦途》、《中国铁路协作曲》等著作,获国家大奖和省级文学奖20余次,作品入录《中国新文学大系》;
在国家研究、周易研究和风水学应用方面独树一帜,20年来孜孜不倦于儒释道三教的普及解脱,在《中国文化报》、《禅露》《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有《国学碎语》多个专栏,在香港三联书店有《雷铎国学小丛书》系列,囊括周易、孔孟、老庄、风水、相学、禅宗、中医和养生、鬼谷子和孙子兵法等诸多领域,并应用于实践,曾任霍英东先生之番禺南沙天后宫风水总设计、潮州、南澳、惠东、肇庆等地方政府历史传统文化顾问;
先生的书法端庄雄浑,书画大师赖少其先生评价“金石味浓,力透纸背”,大鉴藏家吴南生先生评价“读帖很多,功夫很深,但曲高和寡”,香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评价“横平竖直,有庙堂之气”,其书法,多见于旅游名胜黄山、五台山、湘西凤凰、泸沽湖和宗教场所南华寺、天竺寺、肇庆六祖梅庵、广州六榕寺、潮州淡浮院等所收藏,其绘画,师承乃师赖少其先生而又有自家面目,涉猎山水、花卉、仕女等题材,以色彩绚丽和意境古雅见长。
“‘士大夫’是一个流动的概念”
雷铎对目前的状态比较满意,对他来说,无须经商谋生,大部分时间躲在书斋里,过着另类怀旧的生活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中国文坛活跃的青年作家张培忠曾说“雷铎是他们这一辈人的最后一个士大夫”,雷锋则把“士”和“大夫”分开解析:“士”是指读书人,这些人有书生本色;“大夫”则是属于得到政府承认,有政府头衔的书生中的中产阶级。
他认为时代变了,“任何东西都只是接近,‘士大夫’也是一个流动的概念”,言下之意是今时的“士大夫”其实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往日的“士大夫”。他不买车,不买太多奢华的陈设,却把玩着价值不菲的沉香,抽着一条数千元的“熊猫”香烟,这显然是一位有着特立独行格调的现代“士大夫”。
爱穿香云纱衣衫的雷铎常常戏称“这是我的道具”,言谈之间却真实地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迷恋和热爱。当记者的手机响起,他会感叹:“躲不开的西式生活,好像深山里的牛脖子上的铃铛,走到哪里都能把你找到,多累。”
对于东西方文化的特质,他有自己的理解,运用上更是讲究“互照”。这一个“照”字道出了无尽的“感觉”、“感悟”、“体验”。
做学问要注意‘互照’
雷铎认为国学的概念与汉学、大国学(即广义国学,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华学三大内容要“互参”“互照”,很多时候就汉学而谈汉学就和盲人摸象一样,很难有深切感受和全局把握。雷铎更由此引申出中西文化对比的话题,在他看来,所谓“互照”就是一种比较学。
比如,仅就建筑而言,中式建筑具备谦卑、低矮、阴柔、向内并由此走向和谐的特质;西式建筑则凸现了征服、高昂阳刚、向上、并由此走向冲突的理念例如,北京天坛占地面积270万平方米但是主体建筑高度不过38米,整个天坛以其巨大的面积加上一点点的建筑物就创造出比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建筑更令为之感叹为之敬畏的观感,这就是中式建筑的魅力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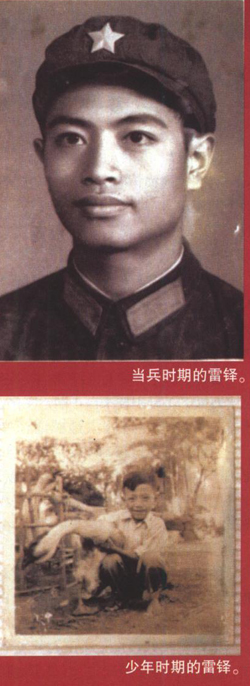
由此话题延伸,雷铎认为,中学西学各有长处,有点像治疗急性病用西医效果更好,而治疗慢性病则用中药更好。西方的长处是工具主义的科学和方法学:西方文化追求人本主义但究其实西人骨子里是形而上意味浓重的神本主义:因为有宗教信仰的存在,相信“三尺之上有神明”,西方人比较讲诚信。而国人自五四之后,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缺乏宗教信仰,儒学也只是教人“慎独”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国人讲诚信,要求他们在无人可见的地方也不要作奸犯科,难度显然很大。
记者随即表示:“法律无法监管的某些问题,其实也可以尝试用道德提升来解决。”雷铎回应道:“宗教信仰也是道德的一部分,索罗斯的名言是’人为的制度永远有漏洞’,最终还是应该让人本身有所敬畏,法律是金字塔的底部,中间是有一定标准的仁义道德,金字塔的最上面是没有止境的慈悲和善行。”
自信的雷铎由文学、艺术创作到周易、风水、禅宗研究,以一人之力跨越多个领域,从未有过力不从心的时候。他不无自得地表示,“多少有一些天份”,所以每进入一个领域都比较顺利。雷铎潜心文学时,他每转换一种文体,首发必然命中,而且常常首发获奖,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规律。雷铎写作惯于一遍成稿,不再回头修改。雷铎回避任何关于自己“成就最大的领域”的提问,而是说起了关于机场的话题:“我昨晚刚刚从汕头回来,汕头机场很冷清,感觉像‘我自己的机场’;到了广州新白云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飞机起起落落,人群熙熙攘攘。现在的我很忙乱,有点像白云机场,但不单一。我做学问时,有点像在乡下的杂货铺的仓库里,找东西去组装某种物件,我比较惯于在不同的学科门类之间做比较、打游击,因而反而容易有一些别人没有发现的心得。”
“吃了一年半蜂王浆”
问起雷铎何以总是跨学科,甚至跨行业,雷铎曾经从诗人到作家、再到学者、再到书画家,而仅学者一项,便涉猎易经、老庄、孔孟、佛家和禅宗、中医和养生、鬼谷子和兵法等等,何以能够轻松自如地“变脸”转换?雷铎只是以恩师饶宗颐的一句话作答:“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读大学。”听者不禁笑了起来,他一本正经地继续解释:“饶宗颐先生说:读大学可能就一辈子固定在一个研究方向上了。我的学历在社科院最低,只在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过两年大专班,但那真是一个超级研究生班,授课的老师是吴组湘、丁玲、王蒙、谢冕、李泽厚等等当时中国最顶尖的作家和各行各当最有名的名家,莫言李存葆钱钢和我是同学,除去半年时间实习,我们实际上只读了一年半书,所以,后来我们这帮同学开玩笑说,我们有幸吃了一年半的蜂王浆。”
雷铎的父亲曾经是粤东农民诗人,雷铎自小受父亲影响很深。解放初期,当时雷家藏书呈落落大满之势,从《四书五经》到延安整风运动的原始书籍无所不包,少年雷铎便在这书香之间流连忘返,三年级便已经看完鲁迅的著作《野草》和《呐喊》。雷铎心中文学、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