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比利时
作者:比尔.布莱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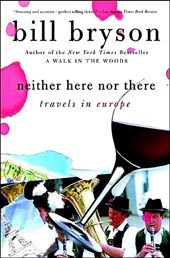
译:顾墟
文:[美] 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
比尔·布莱森,1951年生于美国衣阿华州。1973年往欧洲自助旅行,于英国结识发妻,后遂移居不列颠。为《泰晤士报》、《独立报》撰稿多年,亦写游记。1995年携妻儿五口返美。2003年复之英伦居住(窃恐至今未归)。文风善调笑戏谑,雅俗共赏。代表作《失落的大洲》、《母语》、《小林漫步》等。
《不是故乡非客乡:旅欧纪游》堪称其扛鼎之作。书中以时庄时谐的文字记叙了他“踏平坎坷又出发,一路欢歌向天涯”——从欧陆最北端的城市海墨法斯特,一直到雄踞亚欧泾渭的伊斯坦布尔。随着书页翻动而漾开去的笑声里也激荡出作者对欧洲文化传统的崇敬和山水云烟的痴迷,中间更每每掺以“犬儒”派讽俗讥世的花腔。拙译为该书第六章。
一
我坐着火车在比利时到处转悠,舒舒服服,清清闲闲地过了几天。这么多国家里,比利时可算是挺招人迷的。它可完全不是一个国家哦,而是两个:北部说德语的佛兰德斯和南部说法语的瓦隆。南部集中了最秀雅的风景、最精致的村落、最可口的肴馔,与此俱来的便是高卢传统下消享红尘世界各色清福的秘技了。而北方则有最繁荣的城市、最华美的博物馆和教堂,还有港口、沿海度假胜地、稠密的人口和最集中的钱财。
弗莱芒人受不了瓦隆人,瓦隆人也受不了弗莱芒人。可是你只要跟这两族人稍稍聊上几句就会明白,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原因是他们更加鄙夷共同的“高邻”法兰西人和尼德兰人。有一回,我和一个说德语的比利时当地人在安特卫普逛了一天。在每个街拐角,他都会瞥瞥眼睛,暗示我去看某对表情无辜的男女,并且极其不屑地低声对我说:“尼德兰人!”而我无法将尼德兰人和弗莱芒人甄别开来,对此他大为惊讶。
你一定会问他们为啥这么恨尼德兰人,弗莱芒人对此就有点含糊其辞了。据我所闻,他们抱怨的一个普遍理由就是尼德兰人常常在你家里开饭的那一刻不请自来,且慢说吃你个措手不及,就是丁点菲仪也是不备的。“噢,原来和俺们那嘎嗒的苏格兰人一个德性。”我也来帮帮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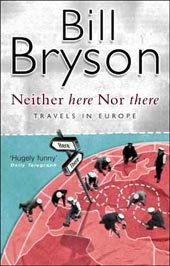
后来我对这个国度有了颇深入的了解。那是在安特卫普呆了一下午,参观了那座有名的罗马教堂,后来就流连到傍晚,泡了很多家酒吧。说起那些酒吧的数量之巨和品位之高,堪称冠绝欧洲。空间小巧,烟香缥缈,惬意得就像是尼格尔·劳森[注:英国前户部大臣,议会中常穿双排扣马甲。]的马褂一般。屋里的墙板都是暗色调,灯光昏黄,可里面总是挤满了意气奋发、兴高采烈的人们,玩得开心极了。在这座城市里,要想找个人聊上几句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当地人心态都很开放,而且他们的英文几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呢。我曾经跟两个年轻的马路清洁工人攀谈过一个钟头,那时正值他们下班回家,路上停下来买杯饮料喝。除了北欧,一个外乡人还能够在其他什么地方用母语同“马路天使”们交谈呢?
一次又一次,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他们对我们是多么了解,而我们对他们则是多么无知啊!你可以读到几个月以来的英国报纸,读到有史以来的美国报纸,却看不到一篇关于比利时的新闻报道。可那里依旧在发生有趣的事情。
就说“匿迹危”匪帮吧,那可是一群在1980年代中期横行该国于一时的恐怖组织(都到了能横行比利时的地步了)。时不时的,他们会冲进大卖场或是人气鼎旺的餐馆,挺起机枪一顿猛扫,肆意杀戮——管他是妇是孺,挡我道者必死。脚下尸积如山,他们却只从收银机上抢去一小笔钱,须臾消逝在茫茫夜色中。可其中还有蹊跷呢:这伙匪人从来不曾显露过他们的动机,从来不劫持人质,抢去的钱也从来不超过几百英镑。甚至连个江湖诨号都没有。“匿迹危”这名号是报道他们恶行的刊物所赐,因为他们借以逃遁的交通工具往往是从尼基维郊区偷来的德国大众宝路型小轿车。如火如荼的恐怖活动进行了约摸六个月之后,嘎然而止,从此销声匿迹,不再危害一方了。持枪歹徒一个没抓到,凶器一件没发现,神探们居然至今还不知道他们是何方高人,这样频频出狠手所为哪桩。这还不算咄咄怪事,又算什么呢?但是您或许在报纸里都没读到过关于此事的新闻——在鄙人想来,同样的,这还不算咄咄怪事,又算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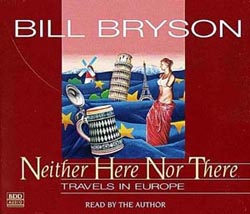
我花了一天时间玩布鲁日。离布鲁塞尔只有三十英里,而景致却是如此美妙,如此无底无尽地绚烂,简直叫人难以相信这是在同一国度。放眼望去,无不美仑美奂——弹格路、碧绿得如啤酒瓶底般的运河水、中世纪遗存下来的尖顶屋宇、集市广场、弥漫着沉沉睡意的公园,一切一切。两百年里,布鲁日——我不清楚为什么大家坚持这样叫它,因为当地人都写作“布鲁吉”,读若“布乳谷”——是欧洲最繁华富庶的城市。然而,随着附近茨文河泥沙的淤积和国际政局白云苍狗的幻变,它竟沦落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后五百年间,欧洲其他城市蓬勃兴隆,不断改新,而布鲁日却少人惦念,乏人问津。以致19世纪华兹华斯[译: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来访时,发现城中街巷碧草深深。还有人告诉我,安特卫普当年更灵,甚至在世纪之交[19世纪末——译者]犹是如此。后来,搞城建开发的来了,把能捣毁的都捣毁了,弄得几乎面目全非。而布鲁日反以不显不达得保全身。

这地方世间罕有。我瞠目结舌地走了一整天。参观了格若宁洁博物馆[注:以收藏当地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品著称。],拜谒了贝居安女修会[注:当地村落,始建于1232年,供基督教女信众修真,现为本笃会修道院。],修会庭院内的水仙摇漾凌波。但一天里的大多数时间,我就是在街上溜达,贪婪地赏鉴着这真善美的富集。这地方的大小也完美不容增损。大得正好有个城市的模样,有书肆和别致的餐馆;小得让人感觉恬淡亲切。差不多一天的时间里,被运河环绕的每一条街道你都可以走到。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居然没有一条脚下的小路不让我油然生起在此定居落户之心,没有一间路过的酒肆我不想进去看个究竟,没有一片风景我不愿独享。难以相信这一切都是活生生的——人们就是每天晚上回到这些屋子里睡觉的,就是在这些小铺子里买东西的,就是在这些小巷子里溜狗的,一辈子就这样慢慢度过,还以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无非就这样呢。这里的居民第一眼看到布鲁塞尔时,必定要惊骇得久久缓不过神来吧。
我在圣雅各布大街上一家酒吧里遇到的那位保险公司核保员惋惜地告诉我,布鲁日一年里有八个月不是人住的,全因为观光客多得成灾,还告诉我一些他认定是骚扰行为的小事,例如有些游客眯缝着眼看他门外信筒里的邮件,有些为了抓拍快照把他院子里的天竺葵踩了个稀巴烂。可他的话我没听进去,部分原因在于他是整个酒吧里——或许是全佛兰德斯——最无聊的屎蛋,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不爱听这个,我要守住这一城幻梦。